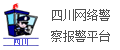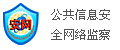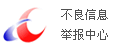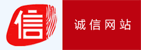(原標題:網約車司機沉浮記)

25日,星巴克清河營南路店,去年5月,王斌(化名)買下一臺汽車,成為了一名網約車司機。今年8月以來,網約車開始面臨更多的行政審核和更少的補貼,王斌還沒嘗到多少甜頭,現在卻被推向去與留的十字路口。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武漢滴滴專車司機正在進行專車服務。他開著一輛奧迪Q3接乘客,收費卻比的士還要便宜。 圖/視覺中國
補貼降低,收入斷崖式下跌,網約車野蠻生長時代結束,司機何去何從
王斌現在有點茫然,不知何去何從。
去年5月,他以20萬元的價格,買下了一輛黑色廣汽本田轎車,成為一名全職網約車司機。
那正是網約車平臺激戰正酣、攻城略地的關鍵年份。滴滴、優步等幾家網約車平臺為了搶占市場,瘋狂燒錢,大打補貼戰。
王斌覺得自己的生活一下子變得金燦燦的——他從月薪五六千元的快遞員,一躍變成月入兩三萬的中產。一不小心,就實現了階層的跨越。
在北京,像王斌這樣的網約車司機有9.5萬,他們一度沉醉于分享經濟帶來的紅利中。有人甚至覺得,自己就是雷軍口中那只在風口里飛起來的豬。
但好景不長。今年春節后,王斌明顯感覺到,補貼降低,收入斷崖式下跌,每天還面臨著被交管部門罰款的危險。他身邊的朋友們陸續轉行。
7月28日,交通運輸部聯合公安部等七部門公布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網約車獲得合法地位,各地也將在11月1日前落實細則;8月1日,滴滴和優步宣布合并。
政策變化和壟斷巨頭醞釀誕生,這意味著,網約車行業將面臨更多的行政許可和更少的補貼。
在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出行方式和網約車司機的生活后,網約車野蠻生長的時代結束了。
王斌們還沒來得及咀嚼分享經濟的成果,又被推向了去與留的十字路口。
飛起來的“豬”
最近,王斌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轉行。
從8月中旬開始,網約車平臺的獎勵和補貼降低,以至可以忽略不計,但王斌還想再觀望一下。
王斌是河南人,今年40歲,已經北漂快十年。妻子和三個孩子在老家,每個月都等著他掙錢養活。他沒有別的手藝,自從買了車,生活就被綁在了上面。
9月22日,王斌特意換上白襯衣、深色西褲、黑皮鞋,去滴滴總部面試。這是成為滴滴認證專車司機的其中一環。獲得認證后,他將會被系統優先派單,也更容易接到優質單。
根據即將施行的網約車新政,通過平臺的認證后,他還要考取專門針對網約車的運輸證和駕駛員證,才能成為一名合法的網約車司機。
去年,他剛加入網約車行業時,手續還相當簡單。只要拿身份證和駕駛證在網約車平臺上注冊通過,當天就能上路運營。
網約車和傳統出租車行業完全不同——網約車司機不用像出租車司機一樣面對嚴格的準入管制,也不需要向出租車公司繳納“份子錢”。
正是這樣的自由、簡單,吸引了大批嘗鮮者。
最初,網約車平臺們打出了“分享經濟”的旗號,希望在大量閑置的車輛與龐大的出行需求之間建立橋梁。滴滴專車就曾打出“自由工作、更高收入、美好出行、你我共享”的廣告來招募司機。
今年6月,滴滴還出版了名為《滴滴:分享經濟改變中國》的書,介紹傳統行業如何搭上分享經濟的順風車。前言里,滴滴出行創始人兼CEO程維寫道“分享經濟浪潮,中國應引領世界”。
那時候,坊間到處都是關于網約車司機的財富神話——有司機連開48小時,掙了4000塊;有媒體報道,一位杭州的網約車司機,用8個月時間,賺了80萬。
所有的信息似乎都在告訴觀望者,順應互聯網發展潮流,成為一名網約車司機吧,這份職業可以滿足你對財富和自由的全部想象。
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一樣,王斌是沖著“更高收入”去的。他辭去了快遞員的工作,借錢買了一輛廣汽本田,一頭扎進了網約車司機大軍。
優步是他最早接觸的平臺。當時,優步正在推行“每周拉滿70單保底7000元”的獎勵政策。做網約車司機的第一個禮拜,王斌就獲得了7000元的流水——這比他當快遞員時的月薪還要高2000元。
“終于找到掙錢的感覺了。”他第一次覺得,路邊那些林立的大飯店,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走進去了”。
21歲的北京人金正宇比王斌早開半年網約車。他比王斌興奮多了。從月薪1800塊的實習廚師,搖身變成月入兩三萬的網約車司機。
“就好像在吃饅頭,突然可以去吃金錢豹了,而且不是自助,是點餐的那種。”他說。
雷軍說,只要站在風口,豬都可以飛起來。金正宇覺得,他就是那只豬。
拼命跑
王斌樂于看到平臺之間開戰。戰場彌漫的硝煙,最后都會以各種形式,具化成司機們口袋里的一摞摞鈔票。
2015年是戰爭白熱化的一年。優步創始人、CEO特拉維斯·卡蘭尼克曾公開說,滴滴每年要花40億美元補貼司機。滴滴副總裁陶然則隔空反擊,優步在2015年燒錢補貼20億美元。
對司機的補貼政策每天都在變化,但能感覺出平臺間的“互動”——滴滴打出平峰時段2倍的獎勵,優步就會出臺滿12單幾百塊的獎勵;反之亦然。
司機們是絕對受益者。兼職司機小佟,在一家教育軟件公司做動畫設計,他晚上六點下班后接單,到晚上十一點回家,一周也能掙一千塊。他正職的月薪也只有五千塊。
王斌同時使用三部手機,裝上滴滴、優步、易到用車三個APP,對比三家當天的補貼政策,再決定使用哪家平臺出車。
“‘戰爭’對我們來說是好事,和平就沒戲了。”有司機深諳燒錢大戰的真諦。
但大部分司機都知道,高補貼不會持久,如果一方資源耗盡,他們的紅利也就走到了盡頭。
紅利稍縱即逝,對抗它的方式,就是“拼命跑”。
根據滴滴和優步的獎勵政策,前一天接的單數越多,第二天的獎勵越豐厚。王斌調整了作息時間,上午五六點出門,晚上十二點回到天通苑的出租屋里睡覺。
但獎勵政策有魔力,作息根本沒法規律。
夜里,王斌本來已經困得不行,頭靠在座椅上,一兩分鐘就能睡著。但一聽到手機APP傳來的接單提示音,“整個人立馬就精神了”。
有好幾次,王斌一直接單到凌晨兩點。回家睡覺不到三個小時,早上五六點起床,繼續出車。
為了沖金牌司機,限號時,王斌也不休息了,待在五環外拉活。
一次,走在四環上,王斌突然斷片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他還納悶,為什么車上有個陌生人。回過神來才發現,他在接單,后座上是乘客。
有兩個月的時間,金正宇甚至沒顧得上回通州的家。
他帶著換洗的衣服,就住在車上。困了就找個停車位,在后座瞇會兒;想洗澡了就找個澡堂子。
那是滴滴快車翻倍獎勵1.8倍、每天完成25單獎勵180元的時期。金正宇看著手機APP里的提現金額,只有一個感覺——刺激。
他記得,那時候,眼里只有APP里的數字,其他都看不到。
去年年末,有一周,滴滴打出了全天5.5倍的獎勵政策。金正宇在國貿橋下看到,保時捷、瑪莎拉蒂全都出動了。往車里一瞅,中控臺上放著手機,一看就是拉“滴滴”的。
再一打聽,不少人工作也不干了,請假出來拉活兒。
瘋狂過后,一條新聞給了王斌當頭一棒——一位網約車司機,因為工作太拼命,猝死了。
金正宇也在連開兩個月車后走進了醫院。他經常斷片,走在路上,紅綠燈都分辨不了。醫生告訴他,過度勞累,休息休息就好了。
持續疲勞駕駛,存在極大隱患。據新華社報道,在2015年,深圳市網約車共發生交通違法75.6萬宗,上報涉網約車交通事故共3653宗,疲勞駕駛、帶病上崗、駕駛員載客途中猝死的情況都存在。
灰色地帶
高收益的誘惑下,除了過度勞累,王斌們還要承擔高風險。
網約車在成立之初,一直是執法部門打擊的重點。但又屢禁不止。
在北京,1996年,出租車的數量約為6.7萬輛,在之后長達20年的時間里,這個數字幾乎不變。但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從1996年的1259萬人,增長到了2016年年初的2190萬人。
這意味著,北京市的出租車萬人擁有量嚴重不足。
在體制的灰色地帶和龐大的市場需求中,網約車野蠻生長。
王斌以前也開過黑車,早知道自己是非法的。接單時,他們會盡量避開人流量高的機場、火車站、醫院等周邊區域——在這些地方,都會有交管部門的執法人員蹲守。一旦被抓,最高面臨兩萬元的罰款。
跑的時間長了,北京城里哪些地方有風險,大家心里都有譜兒——金融大街、西直門凱德mall、宋家莊地鐵站、歡樂谷等地都需要提高警惕。
司機們也形成了攻守同盟,有人在某個路段被抓,大家會在微信群里通傳,“有人在XX路段被抓,盡量繞行”。
高危時期,網約車平臺也會為司機們發送短信,提示繞行路線。
但還是有撞到槍口上的時候。
有一次,金正宇在朝陽大悅城附近被查。執法人員問他,后座是誰。他回,我妹妹。妹妹叫啥?他編了個名字。對方轉頭問乘客,乘客無異議。
執法人員一走,金正宇趕忙說謝謝,還幫乘客免了單。
這也是大部分司機應對檢查的策略——乘客一上車,就溝通好兩人之間的關系和雙方姓名,碰到執法檢查,一起“串供”。
王斌就沒這么幸運了。去年冬天的一個上午,他在南苑機場的停車場被查,罰單金額一萬五。
王斌跟作賊一樣,灰溜溜的。他趕緊給所屬的汽車租賃公司打電話,公司跟他說,沒關系,按流程處理,優步會報銷罰款。
那次以后,王斌再也不敢去機場和火車站了,開車路過高危路段,也都覺得“心在顫”。
開了三年網約車,李明一直想不明白,為啥網約車是非法的;如果非法,為什么不查封滴滴等網約車平臺。
上世紀90年代,他曾開過幾年出租車。他知道,是出租車滿足不了人們的用車需求,網約車才應運而生。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宏觀層面的政策有松動,政府開始研究政策,讓網約車合法化。
李明覺得更尷尬了。在沒有說它合法之前,交管部門還是得去打擊。那種感覺就好像,抓不著你就是合法的,抓著你就是違法的。
網約車的出現,分走了原本屬于出租車的部分“蛋糕”。在一些城市,陸續出現出租車司機罷運維權事件,在天津,甚至上演了出租車司機和網約車司機在路邊沖突的一幕。
好在,北京人多,市場夠大,網約車和出租車的矛盾并不那么明顯。
在夏天的午后,看著天津網約車司機和的哥“火拼”的新聞,北京的網約車司機和的哥們還能坐一起乘乘涼、聊聊天。偶爾冒出幾句的哥的抱怨,“你們一來,我每天的收入少了七十啦”。
“最后的狂歡”
轉折點發生在今年春節后。商業大佬們的市場爭奪戰漸入尾聲。
司機們明顯覺得,補貼慢慢減少了。比如,以前全天2倍的獎勵,逐漸變成高峰2倍,平峰1.8倍,緊接著,高峰1.8倍,平峰1.6倍;完成固定單數的成單獎也在下滑,20塊20塊往下降。
有司機總結,“溫水煮青蛙”。
沒了補貼和獎勵,司機的收益大大縮水。王斌舉例,空駛4公里去接乘客,而后行程3公里,乘客付費10元,扣除20%平臺費、保險費等,司機到手不到8元。按每公里油耗0.8元,7公里共計5.6元。加上電話費和車磨損,到司機賬上幾乎沒了。
有司機接了短途的單子,會被其他人嘲笑,“學雷鋒呢”。
眼看無利可圖,兼職司機紛紛退出。但對王斌這樣的全職司機來說,他們的生活已經和這樣新興的產業榮辱與共,說再見并不容易。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專家委員朱巍認為,滴滴和優步資本大戰帶來的市場占有率是虛幻的,就像是在服用興奮劑。“有一天不用了,他到底能跑多快,只能到時候來看一看”。
但司機們無法接受這種收入的斷崖式下跌。
今年4月15日,有人在微信群里號召大家集體停運,讓北京無滴滴優步。他們的訴求是“拒絕低價勞動力,反對高傭金抽成”。
仍然有人出車。王斌當天就出去跑優步,接了20多單,流水八九百元;金正宇當天跑滴滴快車,接了41單。
為了打擊這些不響應號召的司機,部分司機發起了極端的“扎針”行動——他們用滴滴或優步叫車,叫完取消,拉低出車司機的成單率;或者叫到車后,讓單子掛著,拖延時間。
王斌沒有被“扎”,但他覺得,這種做法不太厚道,“大家都不容易,這是兄弟之間放血”。
風波過后,補貼政策恢復了一點。但只持續了大概一周。
大約從那個時候開始,網約車平臺降低了加入標準,越來越多的外地司機加入其中。有些甚至掛著外地車牌,每周定時辦理進京證,迫不及待沖進這座超級大城市,企圖趕上分享經濟紅利的末班車。
他們大部分只有初中文化,曾輾轉廣州、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月只有兩三千元的收入。
來自四川的老王是最近一個月才加入的。他以4000塊錢一個月的價錢租了一輛車和一張北京車牌。
快一個月了,老王才發現,這份職業并沒有老鄉之前描述的那樣迷人。他每天從早上四五點工作到晚上一兩點,每周只有限號才勉強休息一天;他對北京路線不熟,一天也就跑十來單,除去油耗和車磨損,每天到手只有一百多塊,一個月下來也就三千多。還不如在東莞當電工,每月還有五千塊。
“但租車的合同已經簽了,押金也交了,騎虎難下。”他說。
7月20日北京暴雨那天,網約車溢價翻倍,平均下來,每公里司機到手有10塊錢。
“那是最后的狂歡了。”金正宇說,在那之前,他的收入已經下降到每月五六千了。他決定離開——把車租給別人,每個月什么也不做,也能收入3500元。
“隨波逐流”
7月底,網約車合法化的消息傳來。
但前提是,網約車司機需要和傳統出租車司機一樣,通過考試,取得從業資格證,還需要和網約車平臺簽訂勞動合同或協議。
分享經濟似乎變味了。朱巍覺得,分享經濟就是應該讓人和車都有來去的自由。但現在有了太多的限制。
有專家評價,這是把計劃經濟思維強加到了信息社會的經濟發展中。
幾天后,新的消息傳來,滴滴優步合并。這意味著,一家壟斷巨頭就要誕生,網約車司機們再也看不到兩家大戰,也不可能漁翁得利。
王斌知道這一天會到來,只是沒想到這么快。
最近兩個月,工作時間不變,王斌的流水維持在7000元左右,扣除油耗、車磨損,到手差不多5000元,這和他當快遞員時的收入幾乎持平。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點。
他想不到其他的出路。“我和我的車該何去何從,我也很茫然。”
猶豫了一陣,他還是決定追隨滴滴,需要認證就去認證,需要考試便去考試。這是目前最適合他的飯碗了。他很珍惜。
李明今年已經45歲。他知道,這個年紀,找一份有五險一金的穩定工作,基本不太可能。
7月份,他跑去滴滴總部認證,但沒通過。
這兩月,他沒心情出車。妻子似乎沒什么耐心了,飯也不做,李明只能在路邊買份炒餅吃。這時候,他會懷念當年月入兩三萬元的時光——每晚十二點回家,妻子總會從床上爬起來,給他做一盤紅燒肉。真香。
9月24日,王斌收到消息,他獲得了認證。
滴滴也給他列出了服務規范。比如,不得染發,著白襯衣、深色西裝和皮鞋,以及在乘客上車時問“您好”和下車時說“請帶好隨身物品,再見”。
獲得認證后的第二天,王斌花100塊買了兩件白襯衫,天涼了,又打算再置辦一身西裝。
他不怕這些繁文縟節。他只祈禱能順利拿到從業資格證,也不要被北京的地方細則卡住。
實在不行,那就重新回去開黑車,或者,開個燒烤店吧。
最近幾天,王斌所在的微信群里開始流傳神州專車新上線的網約車項目,歡迎私家車主加入,該項目承諾,不收取平臺費。
有人好像看到了新的希望。也有人持懷疑態度,認為這不過又是招攬司機的噱頭。
大家吵吵嚷嚷,又回想起當年各網約車平臺如何大戰,如何招攬司機,以及那些荷包鼓鼓的日子。
有人總結道:“咱們不是弄潮兒,只能隨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