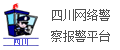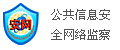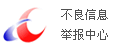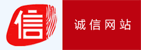保留一份亮堂的文明
眼前,500塊飄著楠木、柏木之香的牌匾,引領著我們走進先祖們吉詳祝福、歌功敬德、正風俗、厚人倫的遠古歲月。
乾隆5年的“杖朝耆年”匾走過了270年。耆代表著70歲,這是對一個一生正氣凜然、直至老年拄杖上朝也要“死諫”的朝廷大員的人格銘記。
光緒34年的繪滿蝙蝠、云扣的雕花匾“蜀國天長”“民懷其恵”“蜀都永賴”,表達著百姓對一方官吏為民所為的心懷感念。
乾隆45年的“艾發重添”是祝壽匾,艾發即白發,祝福添壽長福。它與“福備箕疇”“萱草恒春”匾一樣,古風郁郁,躬行著人間的孝悌善良。
乾隆37年的“梵剎耆英”匾和乾隆45年的“坐破蒲團”匾,顯然是贊嘆德高望重的修行僧人。而民國24年的“銷我億劫”匾乃是修行大德清凈自心、普渡眾生之劫苦的宏真大愿。兩者相輔相承,使我們輕輕觸摸到了埋在歲月深處的信仰的溫暖。
而民國18年銅梁名流劉庚魚送給友兄寶森的“無樂極樂軒”匾,更是獨出機杼,211字的匾文把一個正氣凜然、樂善好施的正人之君、阛阓人杰寫得峭拔偉岸。
民國教育總長傅增湘的顏楷“萱文茂矩”匾雍容謹嚴,近代草圣于右任的“福壽康強”“賢母天荒”匾雄宏婉麗、儀態萬千,而清代翰林院總編撰吳恩鴻的“瓊江書院”匾無不流溢著巴蜀人粗獷、文秀和穩定、內斂。
銅梁人說,這里的500塊匾額原本是1949年前后從各家各戶“沒收”而來,因放在一鄉鎮糧庫充當放糧食的木隔板(防糧食受潮)而躲過了那個動蕩年代破四舊的災難性毀滅,實在是不幸中的一幸。
走在這些歷經浩劫而幸存的牌匾的廊道,我開始想像那個時代。想像那些在門頂、廳堂掛著這些匾額的人家,想像我們的先輩曾經有過的生活。牌匾、祠堂、族譜、書院、家訓、婚俗、祭祀、壽誕……
先人們一代又一代,自律也自在地完成著這些生活必須的儀式,這些儀式最終化成了他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化成了鄉愁,化成了日子,化成了性德,最終化成了一個民族千年的文明。
一塊匾額,濃縮了一段歷史,記載了一個人物故事。兩年前,我到江西萬年參加一個筆會。一群作家,一群張著驚奇、探尋目光的文化人,懷著探訪的心來到營里村。村中有一座南宋著名人士、教育家柴中行開辦的“南溪書院”。柴中行號南溪先生,書院就此得名。
因目睹了朝廷種種腐敗和鬧劇,僅50歲的他,便以年邁為借口退隱于江西萬年營里山中,辦起了南溪書院。
作為古代知識分子,尤其是經歷了30年宦海沉浮之后,柴中行的生命狀態和人格建構不是我們今天能夠輕易窺探得到的。但我們從柴氏家族的譜系里,還是能清晰地讀到他“捐鹽息以惠遠民”;著書批評時政時“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鮮恥,以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淋然紙筆。他任國事官時嚴懲贓吏,任湖南提點刑獄時,豪紳橫行虐民,一一繩之以法。
傳統知識分子大多有退隱情懷,他們在位時文死諫,武死戰。而當他們在政治兇險加身抑或對權勢齷齪無奈無望時,為了人格、氣節的操守,就會尋找一處遠離鬧世的寂林蕪土,或仍作高潔典雅文章,或孜孜授業于鄉間僻野。
躲開了戰亂和權術的渦流,柴中行兄弟肯定把南溪書院辦得有模有樣。否則,在書院走過了474年之后,即清康熙37年,皇廷也就不會將“全德名賢”的匾額授予書院,柴中行后裔們也就不會捐田五百畝以贍書院。
然而,書院現如今也搖搖欲墜,只剩下匾額還昭示我們,漸漸遠去的人和歷史。
我們什么時候把這些連著祖先的養心養德的生命歷法給丟失殆盡了呢?君不見,今天因“丟失”造成的創傷正在殷殷滲血,正在心的深處作疼。
收回思緒,再看匾額博物館,感謝銅梁人在這座燈光并不亮堂的房屋里,小心翼翼保存了一份民族曾經亮堂的文明。
- 下一篇:梁柱之文脈
- 上一篇:我識“蘆山”真面目----王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