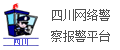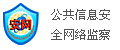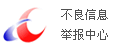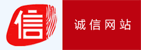歷史悠久且難為人所知的的英式俚語

蘇珊•登特(Susan Dent)是英國最知名的詞匯專家之一。她在新書中詳細分析趣味叢生的外來語和豐富多彩的俚語。這些詞語存世有數百年之久。
"eavesdropper"一詞最初是指借口出去透透氣,站在滴水(eavesdrip)屋檐下與人談話,以期捕捉到鄰院有趣八卦的人。
我的父母曾說,我總是喜歡偷聽別人講話。但是,我可不想聽到一段猥瑣的閑談,我只是想理解對話里的詞匯。我忠實地記錄下偶然聽到的詞語,之后認真鉆研,想要破解這些陌生卻縝密的“密碼”。從此以后,這成為了我一生熱衷的事業。
后來,我用完了許多本筆記;慢慢地,我也成為了一名專業的詞匯研究學者。我發現,從足球粉絲到殯葬員,從特工到彈球玩家以及政治人物,人人都至少從屬于一個社會群落。從群落概念上,我采取的是人類學的研究方式;這些群體更多由職業和興趣決定,而非基因。
我在新書《登特的現代部落》(Dent's Modern Tribes)中談到,了解每個具體群落的最佳方式就是對其語言追根溯源、窮原竟委。
“排除障礙”
“部落式”對話歷史悠久。最早的一些詞典匯集的是黑道上的黑話,躲避當局監控或防止其他“外人”威脅交易的一種方式。很明顯,這也是一種善意的戲謔。一個世紀前,或者更早的時候,如果兩個攔路搶劫的強盜在月黑風高的夜里相遇,他們倆都會互相耳語“這首曲子已付費”,作為從事同一行當的暗號,同時提醒對方,他們絕不可能因為對方耽誤交易。
我從屬的第一個群落是學校——一所女修道院。我們過去把懺悔叫做“泄密測試”(confession test),因為(我猜想)人們在簾子后面把秘密(bean)都講了出來,
而我們每周罪行輕重都可以從神父要求懺悔禱告的長短反映出來。所以,H3并不是一種鉛筆,而是為一般的不當行為念誦三遍圣母經(Hail Marys)(我記得自己從未背過整部玫瑰經,只有贖還最重罪孽才需要這樣做)。
從那時開始,我就參加了各種各樣數不清的團體,每一種都有自己的特色“黑話”。就像所有人一樣,我能根據交往之人所處的團體,在不同”黑話“間轉換自如。正如回家時有些人會換成另一種”黑話“,說天氣用“nesh”(怕冷))而非“cold”(天冷)。我會告訴一同騎車的伙伴,我上一次騎車時很費力(bonk),換句話說,我在精疲力盡的情況下騎車撞上了墻,這事讓我記憶深刻(也很不愉快)。
當然,用“bonking”一詞,可能會讓一些不騎車的人誤解,就像一個外行人聽到一個“twitcher(觀鳥迷)”或“birder(鳥人)”,會以為“漏捕”而心灰意冷,或者聽到“慶祝排除了障礙”(celebrate unblocking the blocker)時,以為是“打亂了思路”。
但是,所有這些詞語都會對他們所處的群落的思維方式產生影響。對于“birder(鳥人)”一詞,你可以感受到別人看到了一只罕見的鳥(an extremely elusive bird 即crippler)、而自己卻錯過了的沮喪感。(另一方面,“Unblocking the blocker”這個短語最終會在你的百鳥譜上出現,因為你看到了一個逃離視線許久的“超級不完美事物”)
“她站在地板上看起來好性感”
我在為新書做調研時,遇到了各種各樣令人心花怒放的驚喜。比如說,建筑工的互相逗樂富有趣味,既點亮了自己的生活,也讓無意間聽到對話的人心生愉快。從他們那里,我學到了一些表達:“鼻涕”(snotter)指任何意外粘在油漆或石膏上的東西,“把肥肉灑到萊昂內爾•里奇(Lionel Richie)的舞池里”(spreading the fat on Lionel Richies dance floor)指給天花板涂灰泥,而“足球運動員加里•內維爾(Gary Neville)慣常一瞥”(footballer Gary Neville gets a frequent looko-in)則表示建筑工需要使用水平儀(或者 “泡泡”)。
熱衷搜集火車機車號碼的人也很有意思,這個群體的年齡段也變得更小,還有更多的女性參與進來。從一群本能夠參加潮人媒體會議的年輕機車號碼迷那里,我學習到了機車“型號”的詞匯,經歷從一個“正常人”(非愛好者)到一個“鐵軌人”(trackbasher)(最狂熱的機車號碼迷)的過程。(我想我只是個“伯特”(bert),即一個普通旅客,腦子里想的只是從A地到B地。)
另外,出租車司機要的不只是“知識”,而是要對倫敦街道路線了如指掌。依靠“山核桃木”(hickory)(dickory dock, 即計時器)謀生,出租車司機創造出了一系列詞語,并讓它們與開車一樣津津樂道。在他們眼里,乘客可稱為“比利•邦特”(Billy Bunters)(英國作家漢密爾頓所著小說中的一個學童punter),男乘客和女乘客分別為“公雞”(cock)和“母雞”(hen),單一乘客是“一枚大頭針”(the single pin),需要跑長途而與司機組成最佳組合的乘客則是“黃金清道夫”(golden roader)。
出租國司機甚至會給倫敦的地標重新命名,國會大廈是“煤氣廠”(Gasworks),國王十字火車站停車處是“香水瓶”(Scent Box),英國廣播公司大廈則是“廢話商店”(Triple Shop)。他們隨意地用這些詞,也會聊那些個坐“霸王車的人”( bilker)——指那些到達目的地不付錢就下車的乘客——的事。
同樣大名遠揚的是有關足球員、梵文學者及管理者的趣事。在足球迷和評論員之間,足球運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語言,“質量”(quality)和“等級”(class)成為了“選擇”(chance)形容詞,“你懂的”(y’know)充斥于談話之中,“看,我說的吧”(like I say)則比史蒂芬•杰拉德( Steven Gerrard)更受歡迎,甚至是在這么說的時候,其實之前從未講過。總而言之,“你沒辦法改變它。”(you couldn’t make it up)。
在所有這些群體中,部落式談話是一種簡單快捷地團結成員的方法。但是,當然也有其它一些群體也有自己的語言:難以破解、保密性強。
一些詞只能是內部人員聽懂,外行人聽起來則云里霧里的。以共濟會成員為例。共濟會的語言里有大量豐富、洪亮的圣經式詞匯,完全與入會儀式相匹配,可是,這卻又與其向公眾開放的意愿相違背。而對軍隊語言來說,行軍密碼直接決定生死存亡。
許多這種不為人知的語言跨越了兩個世界,既為群體提供了肯定性戲謔語,也為現場工作加密。
在類似的交流中,你可能無意中聽到女警說起 “盜車者”(obbo) 的“觀測氣球”(twoccer)的情況——觀察一個偷車賊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盜取車輛);而她的刑事同事則可能在抱怨監獄(nick)里的“工作軸”(job rool)的質量——其實是說警察局的廁紙太過粗糙,就象他們關起來的罪犯一樣粗野(rough)。
以上列舉的只是我找到和記錄下的語言里最喜歡的一小部分,
而在我自己所在的群體里還有其他一些詞語,如說詞典編纂者的“雞蛋玉米”(eggcorn),用來描述像“切奶酪”(' cut to the cheese')這樣的語言誤解成為正確表達的現象;又比如說,攝影師說的“她站在地板上看起來真性感”( 'she's looking hot on the floor')其實并非贊美,而是指模特在這種布景下看起來過于亮眼。我們身邊有著各種各樣的不為外人所知的語言,歷史悠久,內涵豐富,有很多梗和只有圈內人懂的小笑話。
另外,我們還能確定一件事:部落式的談話永遠不會有消失殆盡的一天。就像英語這門語言一樣,我們的群體式談話會一直向前進化,而像我一樣四處打聽的人只能一步一趨地跟著。不過,我會不斷跟進——我還有許多未及填滿的筆記本,我為語言做的“鳥類記錄”才剛剛開了個頭。
- 下一篇:讓有益的“壓力”變成你的“動力”
- 上一篇:記憶力不好會導致肥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