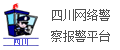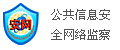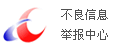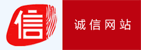柯曼:應機而生-曾憶城的風景攝影

神遇·跡化-曾憶城個展3月24日-5月31日在北京798藝術區舉辦。
開悟之前砍柴挑水;開悟之后砍柴挑水。——禪語
攝影藝術是一種轉寫過程,它作為一種借助于物理和化學原理的技術手段,替觀賞者在攝影者和被攝影的對象間充當轉寫的角色。
盡管攝影過程是借助科學原理和具體器械完成的,它其實是一種冥想的形式或載體,類似在佛教中的“修行”。根據佛教教義,幾乎所有的世俗活動都可以融入這種日常的聞思修過程。而且,攝影作為這一修行過程的媒介及過程,它具備培養內觀,和其他開悟和得智慧的那些必要特征,如:對當下的專注;對緣起緣落的觀想;隨緣隨性的了解;接受無常的坦然。
以上這些特征都體現在曾憶城的作品中,他以攝影為媒介,呈現自己和物質世界之間一種內觀的關系,并邀請觀賞者參與其中。
與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山水畫傳統一脈相承,在曾憶城的山水攝影作品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感知到他的作品與物質世界以及中國哲學中精神世界的“心”或“心靈” 高切合度。在他的作品里,通過使用和前人一樣程度的耐心去觀察當下的風物,以及用和前人一樣的能力來表現一種出世的內觀,他表現了和中國畫在表現自然方面的相似之處。
曾憶城一般地常規做法是摒棄了豐富的色彩,幾乎僅采用黑白灰三色,消解了濃烈色彩可能帶來的刺激和干擾。他不像一些風物攝影師追求三維幻象,而是刻意地采取平面化視角,不動聲色而又果斷地將景物置于全景式的、二維的留白里。如此將觀賞者的注意力吸引到這些留白上,它不再是一種缺位,而是一種存在,與其襯托物一樣躲不過被欣賞的可能。
“應機而生”這句話可用來解釋,這些畫面中隨時飛入的鳥,仿佛在向我們證實那些全景中若隱若現的丘陵和山峰是實相。曾憶城在創作時拆解了全景的繁雜,僅保留少許局部細節來凸顯景物的輪廓以及弱化那些被時空雕琢而成的獨特風姿。仿佛被云朵遮擋或如同柔光中剪影,這些去物質化后的自然景象如虛空中的行星,似乎脫離了地球表面,失重地漂浮在屬于它們自己的自由王國。具有矛盾意味地是,這樣的結果表明曾憶城捕捉到并向我們傳遞的飛逝一瞥的永恒,盡管衡靜久遠,卻又是不斷演生變化的。
這一點也同樣體現在《一時一地》那組更私密的,近景的風景畫面中。稀疏、簡約的畫面擷取了物質世界的—睥—一莖野草,一截孤枝,還有有一只不期而遇的飛鳥,為了它的到來,曾憶城不得不耐心等待,可見他創作過程的良苦用心。然而,這種創作方式和作者的隨緣并不矛盾,和傳統水墨畫家為了下筆瞬間的動作能夠凝練和表達心靈影像時所做的精制功課并無二致。正如攝影師和攝影理論家理查德·克爾斯特爾在釋義埃德加·艾倫·波時所說:“只有極致的理性才可以隨性而發,除此之外都只是沖動而已”。
這一系列的嘗試,體現了曾憶城那么舉重若輕地完成了對傳統最深切的尊重。但這僅僅是他全部作品的一小部分,是他探索未知領域的出發點而已。他的探索還包括:《Dachau》系列引起恐怖遐想的組圖,展示一個臭名昭著的納粹集中營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空間及器具;《交流》是以日本龍安寺那樣的設計精美的禪園為背景,記錄攝影師本人一系列動作的作品;《婚禮》記錄了他為慶祝朋友婚姻而做的兩個象征性的行為;《我們始終沒有牽手旅行》一組小型相機拍攝的黑白照片,其上附有含義隱晦、互相照應的文字;《鏡花緣》則呈現出明顯的后現代主義風格,每個場景都精心編導,色彩明麗。
其中某些作品與當代行為藝術和概念藝術不可避免地產生交集,然而,曾憶城將其根植于他一而貫之的靈性戒律中,確保對行為的記錄仍然能夠作為完全獨立的作品引發共鳴,而不像許多行為藝術和概念藝術的照片那樣,僅僅起到記錄的作用。曾憶城拍攝的畫面并不是對其思想的簡單詮釋和描繪,相反地,是他的思想形象化為畫面。
蘇格拉底說“不加思索的人生毫無價值”。而大部分的攝影活動,我們都有充分地理由認為他們草率和膚淺的,或者正像蘇格拉底說的那樣“不假思索的”。從專業圈子里的狗仔隊對名人的無恥追拍以及時尚界的張揚拍攝,到業余選手單一無味的旅游快照以及無休止的隨意自拍,攝影技術被這個世界已經無可救藥地用濫,用低,用得不假思索了。
我們可能可以說這也在情理之中,因為攝影只不過是底片記錄物體表面反射光而已。然而,曾憶城的作品表明,有這樣一些攝影師,他們會把光學和化學原理及其名不副實的局限性視為一種愉悅的挑戰,一種探索光的邀請,去挖掘在表面下的深意和如何將那些深意浮現在表面之上。
在西方,也許從麥納·懷特(1908-1976)的作品開始,攝影就成為一種顯性的靈性修行方式。麥納·懷特是一名頗有影響力的攝影家、攝影理論家、教師、作家、編輯、策展人,也是基督教神秘主義與佛教哲學的獨特混合載體。他聲稱攝影師和光這種原始材料的互動最終取決于不同層次的精神活動,并試圖在他最后一次重要嘗試——名為Light7 (通往第七能量之光)的群展和專著中證明這一點。
無論看起來多么晦澀難懂,也不論你是否同意,懷特表達了一種概念,一種和他之前的諸如愛德華·韋斯頓、安塞爾·亞當斯和溫·布洛克等攝影家們作品對攝影媒介的理解如出一轍的看法。事實上,懷特的觀點可以追溯至20世紀初的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和赫伯特·格里森以及19世紀后半葉的彼得·亨利·艾默生:攝影術可以超越其機械層面,照片可以超越這個名字的字面含義。事實上,他們認為一張照片不一定與其拍攝對象一致,或者用懷特的話說,“我們拍攝時,不僅僅要拍物體本身,還要拍出它的弦外之音。”在他們看來,攝影可以被視為隱喻,而可以被當做一種語言傳達詩情畫意。
目前,西方攝影作品及其理念星星點點地傳到了中國大陸,情形并不令人滿意;同樣地,中國攝影作品及其理念目前也只是零零星星地傳到了西方,兩者之間還不具備對話的平臺。因此,我們很難追溯出兩者之間的關聯,而僅僅最大限度地看到兩者在攝影態度,方法和手段上的相似性上,看到兩者間存在平行和對應而已。然而,我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在世界各地與影像相關的活動大部分是缺乏思想深度的,如果我們把攝影媒介當作一種修行,其實它是一種賦予物質世界靈性的活動,由此也就促成了內觀。正如曾憶城的作品所呈現的那樣,攝影師們不論身處何地,常常能夠通過這種方式建立媒介工具、材料(對象)和過程之間的關系,這樣,他們也加入了沒有地域和政治疆界限定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