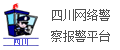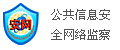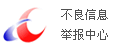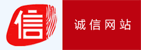中印戰爭老兵盼國家獎章50年未果 花30元自制
原標題:發給自己的獎章 老兵期待1962年中印戰爭的國家紀念
30元,是制作一枚獎章的價格;
50年,是等待一枚獎章的時間。
經歷了對公開紀念漫長的等待后,都江堰、彭州兩地的中國對印度自衛反擊戰的老兵們,決定自己給自己發一枚獎章。
記者 雍興中 圖 翁洹 實習生 田香凝
和很多老兵一樣,提議給自己發獎章的彭維松,也是在退休之后,越發在意那場戰爭一直未有官方紀念。每年10月,他總會打開新聞聯播,看是否有關于中印戰爭的報道。有是有,但都是報道戰敗國印度方面的有關活動。
1962年11月18日,他們都是55師163團的成員,在中印邊境西山口打響了戰斗。是役是中印戰爭的最后一仗,爾后堪稱大捷的中國宣布全面停火,和平在刻意的低調中維持至今。
在國內,人們對那場戰爭知之甚少,曾經二十上下的參戰士兵,在邁入古稀之年時,也走進了被遺忘的角落。他們尋找著彼此,共同的記憶在白發和皺紋間流淌,如今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不要忘記自己。
發獎章的提議獲得全體通過,全體是多少?70人。2012年建軍節前夕,在彭州的一處農家樂,老兵們領到了自制的獎章,戴著它合影留念,喜氣自溢。這讓沒有參加的老兵十分羨慕,也希望有一枚,負責制作的楊建余說,沒有那么多了,只做了100枚。
而這100枚獎章,在那之后的一年,也沒有什么機會與人見面。它能夠出現在什么場合呢?隆重的紀念大會,還是家人團聚的飯桌?事實上只有記者到訪,老兵們才會把它從小盒子里拿出來,講述那些家人早已聽膩的故事。
“話可是中央說的”
1962年的冬天,青海民和縣163團2營營部,通信員楊建余守著步話機。
西山口戰役已經結束一個多月了,11月22日毛主席命令全線停火,12月1日又主動后撤,原本秘密入藏的163團很快回到了民和縣駐地。楊建余記得,出發時部隊把來不及收的青稞全扔在了山上,回來時都不見了,就像一些戰友再也沒有回來。
戰場上,朝夕相伴的步話機是楊建余的保護神。在西山口沖一段300米的封鎖線時,每跑10米就要臥倒,楊建余看到有人犧牲,有人躺倒腿不住地打顫,而他總是用一種不標準的姿勢,將背上的步話機迎向子彈,希望最后自己被擊中時威力還不致死。最后,當他們沖到碉堡前,看到了小山一樣的機槍彈殼。敵人被擊潰了,楊建余和步話機都沒事,依然可以回到后方享受平靜。
這一天的平靜,是被中央慰問團打破的。戰友跑來告訴他,中央派來的慰問團在團部禮堂演出。楊建余這一年22歲,還是喜歡熱鬧的年紀。他跑向團部禮堂,看到那里已是人山人海。中央慰問團帶來了一支樂隊,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樂器,聽人說是一支管弦樂隊。很多年后,楊建余已記不得那天觀看了什么樣的舞蹈,聽了什么樣的相聲,他只記得回到營房,部隊發給了他一大堆中央慰問團的慰問品,其中有一條雪白的毛巾,上面寫著——
“不愧為偉大的人民,不愧為偉大的軍隊。”
當獎章從天鵝絨的小盒子里被拿出來,看到正面“中印反擊戰”五個字,不知道的人會以為這是老人跨越半個世紀的珍藏,但實際上它被制作出來剛好一年。
72歲的楊建余一手拎起獎章,一手翻過它的背面,獎章上的話來自1962年的中央慰問團,樣式則完全模仿了軍功章。認真地解釋:“東西是我們自己做的,這兩句話可是中央說的。”
在老兵們的記憶中,50年前到訪的中央慰問團,是國家對中國對印反擊戰唯一也是最后的紀念。演出之后發的每一件慰問品,老兵們說起來如數家珍,那包括:三五個信封,一疊信箋,一只搪瓷茶杯,一支英雄牌鋼筆,還有一條雪白的毛巾。
這些不過是日常用品,在普通人家不知要更換幾何,老兵卻記得每一個卷走記憶的漩渦。
“搪瓷缸在甘肅坐火車時丟了。”曾在炮營服役的劉成全語調沉緩地回憶,當他轉業到劉家峽水電站,時間就開始一點點剝離他與軍旅的聯系,“英雄鋼筆在學習安全常識時,不小心擠壞了;信箋丟到劉家峽水庫了;有一年家里著火,白毛巾燒掉了。”
毛巾只有少數人還保留著,只是雪白已經變成了鵝黃,但有一份精神寄托附著其上。給自己制作一枚獎章,便是緣于這份寄托無處安放。
2011年11月18日,彭州原163團戰友第六次聚會。這是多年前西山口戰役打響的日子,在老兵們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的刻印。聚會是楊建余和戰友何洪昌發起的,這一天大家聊得最多的是:眼看第二年就是中印戰爭50周年了。
有人提議,聯名給中央軍委寫封信,給所有參戰的老兵發一個50周年的獎章。這個建議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大家考慮起如何行文、如何措詞。
這時來自都江堰的戰友彭維松說:“干脆我們自己做個獎章吧。”
這個提議先是引起了一陣訝異。“獎章只有軍委才能發嘛,我們發算什么?”有人說。但楊建余和何洪昌都覺得可以:“軍委發的叫軍功章,我們自己做的是紀念章,沒啥子不可以。”
“開個亞運會都有紀念章,我們為什么不能有?”彭維松看來,是不是官方發的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向后人證明,老兵們曾參加過那一場戰斗。
最后,給軍委的信仍然要寫,而發獎章的動議也被一致通過。72歲的楊建余和73歲的何洪昌開始操持這件事情。
次年7月,何洪昌讓女兒在網絡上找好了廠家,楊建余通過親戚在成都談好了價格,每枚30元,然后由何洪昌往返成都與廠家商量定稿。
何洪昌回憶,讓他來跑這件事,是因為老兵中他的身體還算好,可年齡確實不饒人。“第一次從彭州去成都,轉了三次車才找到廠家。”到的時候已經是12點了,老板不在,在7月的酷熱里,他等到下午3點才辦成了事兒。
后來何洪昌往返5次只為商定好獎章的細節,最特別的就是要在背面加上一句話:“不愧為偉大的人民,不愧為偉大的軍隊。”
50年前,毛巾上印的就是這句話。
“刻骨銘心,怎么也忘不了”
1962年11月17日,夜,佳山口沒有月亮。
163團接到的指令是在18日正面主攻西山口,而西山口前的佳山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勢。3營接下了拿下佳山口的任務,預計傷亡會達到90%。
彭維松什么也看不見,他的視野內只有戰友的背影。背影跑起來自己也跟著跑,背影蹲下休息自己也蹲下休息。夜間行軍不能有一絲光亮,首長看地圖,也要用三件雨衣遮蔽起來。
白天,他曾看過佳山口。山上長滿了大杜鵑樹,沒有開花,但保持著綠葉,山谷中有流水,森林里有猿猴,深山中還覆有一層新雪,本來是一個景色不錯的地方。
但自從一進山,這里就充滿了危險,原始森林和崇山峻嶺從未給一支軍隊預備過道路。各連原有騾馬馱補給,但進山不久幾匹軍馬就掉進了深澗,不少戰士踩著雪滑進河里,打濕了棉衣棉褲,冷得直哆嗦。剩下的騾馬因此被幸運地放生了。
雪唯一的好處是隨手可以抓到嘴里解渴。出發前,部隊給每人發了一天的給養——炒面和白糖,兩樣吃起來都需要水。戰前吃最后一頓飯時,營長說,多吃點,打起仗來可能一天都吃不上飯。
彭維松是炮連的,心情也并不輕松。他不知道戰斗何時會打響,黑暗與寂靜中,大家的弦都緊繃著。
“啪!”一聲槍響從黑暗中傳來,在寂靜的山中如同驚雷。
50年過去了,回憶仍是鮮活。
“當時3營8連的文方富走火了。”張龍凡是3營的通信兵,記得當時參謀長和副師長氣得要槍斃文方富,因為山的對面就是敵人,隊伍隨時可能暴露。這時8連的指導員站出來說,槍斃又會有槍響,不如等仗打完再說。
幸運的是,佳山口的守軍已經逃走,文方富走火沒有造成嚴重后果。后來的戰斗中他表現勇敢,也就沒人再提槍斃的事。
那之后的很多年,上自廟堂,下至民間,那天的戰事像深山的溪流般靜靜地流淌,也沒什么人再提中印戰爭的事,烙印已經打在老兵記憶中,直到晚年變得越來越清晰。
1965年前后,老兵們各自退伍轉業,有了新的職業和生活。對比參軍的時間,他們的第二職業無疑要長得多,但讓他們念念不忘的,始終是西山口。
這種只有上過戰場才能體驗的感覺,“刻骨銘心,怎么也忘不了。”張龍凡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平時訓練再苦,上戰場就那么一兩天,激烈的戰斗可能就幾個小時,而就這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有的戰友就犧牲了。
“我們那時受的教育,戰友犧牲了,要堅強,要勇敢,心里難過也不會表現出來。”彭維松腦海里始終忘不了一名叫王道樹的戰友,他本來已經去了文工團,打仗時又分了回來,通過封鎖線時犧牲了。和所有老兵一樣,當他講述這段往事時,語速緩慢,目光散開,仿佛看到了戰友犧牲的樣子,或者自己幾乎同時死去。
戰場記憶以年為單位,在腦海里不斷單曲循環,一旦想要找個出口,即使在家人那兒,也要碰一鼻子灰。
“又到這一天了。”每年的11月18日,劉成全都會咕噥這么一句,得到的結果是:“老婆都聽煩了。”
年輕的時候,妻子袁新旭也聽劉成全講打仗的事,聽他講被垂死的印度兵抱住大腿,戰場上戰友在身邊犧牲。但隨著歲月被煙火熏烤,那些有關殘酷與犧
牲的故事,家人們不再聽,劉成全也不再講。
“那些老掉牙的東西沒有用。”袁新旭說,在劉成全家,也就女婿喜歡軍事,愿意聽他講一些。戰爭經歷留給這個家庭僅剩的紀念品,是一個飯盒。那是劉成全在戰場上繳獲的,飯盒一直用到磨破了底。
“那些事,講一次就夠了。”這是大多數老兵家屬的態度,90后的孫輩們甚至會覺得:“這些有什么意思呢?”
當劉成全說戰友們集資做紀念章,需要30元錢時,妻子竟然表示了反對。“你一天天從包包里拿錢出來,誰給你錢呢?”袁新旭說。
“她說我拿回來沒用,我說你不懂,這就是一個紀念。”劉成全說,他這一輩子也算是保家衛國過,拿出獎章,他還可以說他也曾去過戰場。
就在南方周末記者到訪的這天,劉成全珍視的最后一頂軍帽,也終于被證實消失在兒女的幾大箱衣物里了。他的印象中,這頂特殊的軍帽2006年時還在。
劉成全記得特別清楚,當外孫女第一次看見軍帽時,驚訝地說:“外公你還真有這個啊?”
外孫女小時候也聽過劉成全的故事,直到見到軍帽時似乎才真相信了他,這讓劉成全感慨萬千。
當初遭遇家人的反對,他說:“我這一生當中就剩了一頂帽子,就讓我再領個獎章吧。”畢竟30元不是什么大數目,劉成全拿到了這枚獎章。現在,這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紀念。
“真的就只是一個榮譽。”
1962年10月23日,民和縣農場,楊建余和戰友們收割著青稞。
這并不是一項輕松的活。三年困難時期剛剛結束,部隊的標準是每人每月45斤糧,其中還要扣去2斤支援地方建設。對于年輕小伙子來說,只能維持半饑半飽的狀態。
下午5時許,勞累了一天的楊建余正在感到疲憊襲來,進藏對印作戰的命令傳了下來。
對這道命令,戰士們并不意外。上世紀50年代開始,印度一直在邊境上侵擾中國。1961年開始,印軍在西段邊境的中國領土上建立入侵據點。中國進入戰前準備時,戰士們開始學習簡單的英語。
“華落米”、“努提各”和“給烏阿撲”,很多年后,楊建余依然堅持著讓人不知所云的發音,但他也清楚地記得這幾句的中文意思是“跟我走(follow me)”、“不準走(not go)”和“放下槍(give up)”。
在營部,營長只作了簡單的戰前動員就出發了。這已足夠,戰士們積極請戰,當天晚上就有人咬破手指寫下血書。
楊建余寫的,是一封家信。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還有6個弟弟和1個妹妹。快要上戰場了,他并不怕死,只是想告訴母親,作好心理準備,而且他死之后家里還有兄弟可以依靠。
難辦的是這封信無法寄出。平常戰士寄信都是交到團部寄出,但部隊開拔前去西寧乘車后,就不允許再寄信了。
直到部隊開到格爾木,楊建余才找到機會,將信投進了地方上的郵筒。
后來回家探親,楊建余才知道,母親看完那封信,獨自跑到河邊痛哭了一場。
1982年,楊母以花甲之年亡故,楊建余再也體會不到母親的關愛。現在,有誰還會像母親一樣關懷他呢?
當年,他們都甘愿為祖國母親拋灑熱血。“行軍途中,每到宿營地,戰士們不是先休息,而是爭先表決心,寫請戰書。”何洪昌說。
即將進入戰斗的前一晚,連、團領導想將他臨時調換到9連,這個連第二天將擔任主攻西山口的任務,何洪昌表示堅決服從命令。
臨戰那晚很緊張,每個人都在棉衣里面寫上名字,免得犧牲了還不知道是誰。何洪昌在衣服上寫了名字,數了數身上還有七十元錢,然后拿出一張紙條寫下“我犧牲后請將我身上的七十元錢交黨費”,怕母親驟然得知傷心,他又寫下一句“不急于通知我母親”,然后放進衣服口袋。
打下西山口,九連榮獲集體二等功,還出了一個戰斗英雄龐國興,何洪昌本人也被評為三等功。
“立三等功的有個毛主席像章,我就有一個。”很多年后,何洪昌對此感到不滿足,因為像章上沒有任何字樣,看不出來是對參加對印反擊戰嘉獎的。
當老百姓和當兵不一樣,老百姓就是要維持生活,在地方單位一直忙著工作,只有建軍節時會收到單位的問候。“過去30周年、40周年,也沒有紀念,但那時我們這幫人都還在職,想不到這些。”彭維松說。
那時候,士兵們各奔東西,單位不一樣,對退伍軍人的態度也不一樣。有的單位是幾句問候,有的單位是發一張電影票,這還是退伍軍人較多的單位,小單位里便無人在意,而無論哪里,誰也不會關心中印戰爭紀念日。
年輕的時候,老兵們對這些都還無所謂,退休后才越發懷念起部隊。軍旅生涯在他們身上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他們已經習慣于向集體尋找歸宿與認同,當發現“沒人管”時,也就倍感失落。
張龍凡說,退休后起碼建軍節別忘了我們。不要錢,也不要請吃飯,也不用安排什么事做,這就是個榮譽。
老兵們珍視榮譽,有時候甚為敏感。
2007年,民政部發文,調整了部分優撫對象的撫恤補助標準,對在農村和城鎮無工作單位的參戰退役人員,發放了每人每月100元補助。民政部的優撫一貫以貧困群體為對象,在老兵的重點卻看在了“參戰”兩個字上。
“仗打起來,子彈還分農村人、城市人嗎?”何洪昌的話得到了老兵們的贊同。當年參軍的小伙子們,絕大多數都出自農村,只是在轉業后,才變成了城市人。在他們看來,參戰退役人員應該一視同仁,補助發放就不應該分農村還是城市。
成都的老兵劉家豐為此不斷上書,老兵們都簽字附議了,他們中也有不少是農村人。
“我們大部分人生活都還過得去,也不是為了那100塊錢,真的就只是一個榮譽。”彭維松說。
新聞鏈接
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
從1959年開始,印度軍隊在東段越過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在中段、西段越過傳統習慣線,在中國境內建哨設點。1962年7月,印度軍隊公然侵入中國阿克塞欽地區的加勒萬河谷,把中印邊界緊張局勢推到了一觸即發的高危境地。1962年10月至11月間,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爆發。在中國軍隊全面獲勝、印度已經無力再戰的情況下,我方宣布停火,并主動后撤。
只怕慢慢被遺忘
1962年11月18日凌晨,西山口,楊建余遭遇了伏擊。
戰斗打響的時候,全亂了。戰場上火光連天,炮彈、子彈呼嘯,連遠近都聽得出來。楊建余看到到處都是印度的散兵,到處都在交火。身后的戰友說了一聲快走,回頭一看,隊伍全撤了。楊建余趕緊后撤,剛退下來,一陣子彈全打在了原先臥倒的位置。
在海拔5000米的戰場上,楊建余背著七十多斤的步話機,跟著營部四處迂回,氣喘吁吁間,幾十個人退到了一處崖邊,左右都是印度兵。
營長決定用火焰噴射器。這是當時最新的步兵裝備,一個營只配了三具,每具火焰噴射器后面有三根管子,只能發射三次。
長長的火龍噴射而出,楊建余看見凝固汽油四處流淌,流到哪兒燒到哪兒,印度兵落荒而逃。
這場戰斗,楊建余印象最深的死者是營里的一個通信兵,他被自己人走火打傷肚子,痛了一晚上后死在了楊建余面前。
和很多戰爭一樣,中印戰爭的亡靈至今沒有完整的名錄,也沒有公開的祭奠。盡管51年前的世界屋脊之戰已經淡出了社會的記憶。但各地零散的自發紀念一直存在,并根據組織者不同而各具規模。
2012年,新疆、西安等地,都有大型的中印戰爭紀念活動。張龍凡在當年參加了西安的“原步兵第55師參加中印邊境戰斗50周年紀念戰友會”,那一次有六百多人參加。
“這個活動搞得比較好,還出了一本《西山口之戰》的書。”張龍凡說,西安在2010年就開始籌備50周年紀念了,聲勢隆重主要得益于原55師參戰的團級干部、軍級干部組織了起來。
不難理解,當年的參戰人員,有人在軍界榮升,有人在商界取得成功。因此,一些活動不僅組織得有聲有色,還有不少書籍和畫冊出版。
更多的老兵,平凡而普通,他們只能在有限的能力內尋找同袍,往往還并不容易。
1960年,西藏軍區在成都地區招了數千兵員,彭州就有500人,其中有300人到了時稱8062部隊的163團。可就是這批老兵,也直到1998年才有了第一次聚會。
“平常工作都忙,也沒人組織。”楊建余說,那一年他從水電建設總公司退休,感覺可以做這件事了,才和另一位在彭州的戰友何洪昌一起,在建軍節組織了第一次聚會。
聚會很簡樸,楊何二人出資買了點花生、瓜子,還有小桔子,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最后在農家樂共同出資吃一頓飯就是全部的活動。
這已足夠讓老兵們得到快慰。在一個專用的筆記本上,何洪昌認真記下了第一次聚會的情形:由于多年未見,戰友相聚十分親切地敘舊情,話友誼,一時間皆未盡興。
此后,除了2000年到2007年中斷,楊建余和何洪昌每年建軍節都組織大家聚會一次。農家樂里,50元的花生瓜子,就可以讓十多位老人聊上一天。
“我們穿過黃衣服(指軍裝)的,經過部隊這種特殊生活的錘煉,共同語言很多。”何洪昌說,戰友相聚只要見面就是高興的。
風燭殘年的老人們心里很明白,年齡大了,見一次面就少一次。然而,有多少戰友等待著聯絡,又有多少戰友已經故去,這是民間組織者也不知道的。
楊建余和何洪昌14年間組織了7次聚會,只聯絡到了成都地區的七十余名老兵,從未成立正式組織,依靠的也只有人脈聯系。“比如一次聚會他參加了,然后他又說還能聯系到誰誰誰,那就下次聚會又叫上。”
聚會后,彼此聯系增多,楊建余和何洪昌現在也會邀戰友一起打打麻將。那是一種當地人稱為“磨袖子”的玩法,一塊錢一局,彩頭太小,年輕人不屑于參與。
年輕人不能理解的是,即使只是面對面坐著,老人們的相聚也自有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