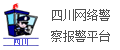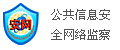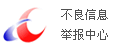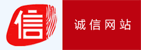別管日本模式、德國模式,垃圾分類該有中國模式
最近,垃圾分類成了持續不斷的熱點話題。多地已經或將建立相關條例,對違反垃圾分類規定的行為設定相應懲罰規則——這一“史上最嚴垃圾分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入我們的生活。
如何看待這一輪垃圾分類?目前的垃圾分類有哪些問題有待優化?帶著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采訪了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蔣建國、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樓紫陽、零廢棄聯盟執委毛達博士,來為我們解讀垃圾分類背后的問題。
垃圾分類該有中國模式
新京報:近段時間,輿論場上聚焦東京垃圾分類模式的比較多。有人稱其并不是好榜樣。你如何評價日本模式?
毛達:我認為應該辯證看待日本模式。就日本自身模式來看,其大多數的分類并不是干濕分開,它分為可燃與不可燃。這是日本垃圾分類的基本模式,是由其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決定的。
但站在更宏觀的角度——世界可持續的固體廢棄物管理的潮流來講,日本模式確實不是最先進的。因為按照聯合國環境署2013年所出的《國家廢棄物管理戰略指南》,一個國家的固廢管理的目標,是將送往填埋和廢物能源利用處置設施的廢物總量減到最少。而日本接近80%的垃圾焚燒,本身就不符合這種潮流和理念。
從分類角度來說,也應批判性地去看待日本模式。日本是抓小放大,抓了20%,分得特別細。這是由其國情決定,或者說也與其后端價值鏈有關,因為人力比較貴,后端的回收產業沒那么發達,它需要前端分得特別細。
目前來講,這肯定不適合我們。如此細致的垃圾分類,需要居民付出足夠的時間成本和生活成本。我們才剛剛起步,重在培育居民的習慣,在目前后端可以實現分揀的情況下,在可回收這一塊,現在沒必要分得那么細。
蔣建國: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推進垃圾分類工作,在多年的探索中,我們參考了發達國家已有的經驗,如今也摸索出了一些有我們自己特色的垃圾分類方式。
而所謂特色,與各個國家的垃圾特性、產生量等息息相關。其一,由于生活習慣、飲食習慣的不同,我國所謂的濕垃圾/廚余垃圾是與國際上不一樣的。其二,從我們垃圾產生量來看,由于我國人口規模遠大于這些國家,因此,單位面積垃圾產生量也非常大。
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以前沒有意識到的一些垃圾產生得非常快,其中一個典型就是外賣、快遞等新型垃圾的產生。
種種情況決定了我們現在制定的垃圾分類方式,不能完全模仿發達國家做法,更不能模仿日本這種分得那么細的做法。
樓紫陽:模式都是人為弄出來的,日本這么做,是由歷史原因、國民素質、家庭模式等多種原因決定的,并不適合我們。
垃圾處理從來沒有說哪個技術更好,哪個技術最差,一定是找適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本身特性的。不能就說日本這種精細化的就好,中國這種就不好。
垃圾分類的正確模式是,后端已有的技術、設備、處理設施需要什么樣的垃圾,決定了我們前端分到什么程度,而并不是人為一拍腦袋誰好就誰來。
垃圾分類沒網傳那么復雜
新京報:您怎么看待這一輪垃圾分類?有無需要改進的地方?
蔣建國:從城市管理角度看,目前的垃圾分類就是大類的粗分。
對于居民而言,首先要把可回收的垃圾分開。所謂可回收垃圾,包括玻璃瓶、金屬廢鐵、塑料、廢紙,以及廢棄衣物等五大類,簡稱“玻金塑紙衣”。這五種,特別是前四種,都是可以賣錢的。
還有一類相對復雜的,就是有害垃圾。有害垃圾包括電池、廢棄藥品等。這些有害垃圾并不經常產生,有的一年也就一兩次。只要做好宣傳,告訴居民哪些是有害垃圾,應該投放到什么點。這種分類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垃圾分類的關鍵在于那些更多的不值錢的東西。簡單來說,最好識別的就是廚余垃圾、其他垃圾,也有地方稱之為濕垃圾、干垃圾。
最近公眾討論比較熱的“哪個是干垃圾,哪個是濕垃圾”,其實討論得過細了。對居民來說,簡單理解哪些是濕垃圾,就是與我們吃的有關的東西,比如剩飯剩菜,其他的也不用管太多,都屬于干垃圾/其他垃圾。
這樣家里也就只需要兩個垃圾桶,并不像網上各種段子、小視頻介紹得那么復雜。
樓紫陽:目前的干濕分類沒有問題,但名字有些別扭。比如,干瓜子殼就是濕垃圾。
毛達:分類方法沒意見,但建議補充回收公告制度,設立“公告回收目錄”。
凡進入“公告回收目錄”的垃圾,要么應屬于國家或地方強制回收的廢棄物,如有害垃圾或餐廚垃圾,要么屬于國家要求企業履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的廢棄物,如電子廢物、紙基復合包裝,要么是基于市場機制,回收再生渠道和設施有相當可靠性的廢棄物,如廢紙板、廢塑料瓶等。
對于目錄之外的廢棄物,如果市民不清楚是否屬于可回收物,可在再生資源回收站進行現場確認,如果回收站不接收,即可投放到其他垃圾或干垃圾桶中。
“公告回收目錄”一旦建立,就應定期更新,因為廢棄物的可回收利用性質會隨社會、經濟和技術條件的變化發生改變。但無論它如何變化,名單是短還是長,讓市民始終接收“一旦分出,就能很好利用”的正向信息,是保持他們分類習慣的一種很好的“長效機制”。
技術有力推動垃圾分類
新京報:在垃圾分類中,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能發揮什么作用?
樓紫陽:事實上,垃圾分類就兩個事情:一是垃圾怎么讓這些產生者按規定分好,在這一部分,如人工智能、攝像頭等技術都大有可為;二是后端的機械化分揀,目前這方面的技術已經相對成熟,當然,還有根據新的技術發展而進一步改進的空間。諸如圖像識別等技術,效果都是看得見的。
蔣建國:傳統的機械分揀等手段不是新鮮事物,關鍵在人工和機械如何結合起來。
這里面涉及一個經濟性原則。高科技的應用與前端的垃圾量有關,幾個瓶子來讓機械分揀,沒有必要。當垃圾集中之后,一個區域、一個城市上萬個瓶子,只通過人工分揀成本太高,這時候就可以通過技術進行自動識別、分揀、分門別類打包。
不論如何,垃圾分類一定要通過源頭的人的配合。離開這個前提,后端再智能,也實現不了垃圾分類的效果。
毛達:首先要說明一點,就是在我們體驗中,行之有效的垃圾分類的基本模式就是,堅持產生者、個人或家庭在源頭進行分類,不管是細還是粗。
因為在源頭分類,我們其實只需要轉換意識,而意識轉換所付出的環境代價極小。真正要付出的代價,是信息溝通與教育這種系統性的工作。而這是我們必然要付出的。
一些新的科技,比如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如果說它的作用是讓我們的教育更精準、更快速,我覺得大有可為。比如,目前有些軟件可以用人工智能技術,去識別一些垃圾屬于哪種類別。
另外一個技術作用于垃圾分類的方式,就是去匿名化。最近,北京垃圾分類“刷臉”開蓋的新聞比較火,其就是一個去匿名化,甚至是走向實名制的一個過程。這些技術比較時髦,能吸引大家注意,本身就能起到一種教育宣傳作用。
這一次我們是認真的
新京報:我們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推動垃圾分類工作,但效果一直不如預期。那么,這一輪垃圾分類,如何避免重蹈之前的困境?
毛達:說實話,我對這一輪的垃圾分類滿懷期待。事實上,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里,明確提出要逐步推行垃圾強制分類制度。這是個擬以制度化的方式來推動的事情,是整個生態文明建設體系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臨時起意。
且今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修訂草案)》,也把垃圾分類作為制度寫進去,這是前所未有的。
我們做垃圾分類,不是說這是國際潮流,也不只是因為我們開始從理論上認識垃圾分類了。而是現實中,不分類混燒、混埋的社會代價有人在承擔了,有人在關注了,也有了對垃圾進行分類的需求。
樓紫陽:我們之前推進的垃圾分類之所以沒有達到預期,主要是末端設施沒有跟上。
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0年,是垃圾分類末端設施“補鈣”時期。比如,修建填埋場、焚燒廠等,這解決的是安全處置、衛生處置問題。到現在,隨著技術發展,我們基本解決了垃圾處理無害化的問題。
無害化后,我們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可以繼續優化。垃圾分類是為優化服務的,重點是提高垃圾的附加值。而通過前端垃圾分類,到后端的有效處理,在生態系統的閉環中,實現垃圾減量目標,是垃圾處理的大趨勢。
垃圾分類工作,不妨“小步快走”
新京報:在垃圾分類的實踐中,也產生了一些問題。未來如何讓居民在便利性與經濟性中找到平衡呢?
蔣建國: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簡單問題復雜化,要在公眾比較容易接受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分類方法。
從政府角度,居民分出來的東西,后端必須有明確出路,系統一定要完善。不能說前端分了,后面又混了,又走了之前效果不好的老路。實際上,打通環節,才能取得垃圾分類的效果。
樓紫陽:垃圾分類需要慢慢推,我一直在說一個詞——“小步快走”,即大原則定了,中間發現問題及時改,改到讓大家滿意。比如,粽葉、榴蓮殼、椰子殼等是干垃圾還是濕垃圾,就可以用黑名單或者白名單的形式列出來。
毛達:垃圾分類確實是要在便利性和經濟性中尋找平衡,目前上海或者其他城市正在做的定時定點收集,就是個好的平衡點。
有人說,垃圾分類習慣養成需要幾十年。其實用不了那么長,主要看想要達到的目標是什么。比如,意大利米蘭從不分類到分類的明顯轉換,也就用了三四年。但如果說要讓垃圾分類理念深入骨髓,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是一代人的時間。(時事訪談員 李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