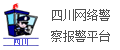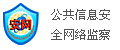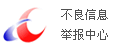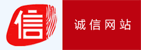為了治好這個病,他不惜走上法庭
核心提示:在我們那一代人的小學語文課文中,有一篇的題目是《給自己寫信的人》,講的其實就是埃爾利希找到治療梅毒有效藥物的故事,但在這
在我們那一代人的小學語文課文中,有一篇的題目是《給自己寫信的人》,講的其實就是埃爾利希找到治療梅毒有效藥物的故事,但在這篇課文里并未出現梅毒的字眼。
我猜測,以當時鄉村小學教師的水平,可能也不知道埃爾利希研究的藥物究竟是治療哪種疾病的。等到各路游醫把治療梅毒性病的小廣告貼遍全國所有電線桿子和廁所墻壁的時候,已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了。
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以有效藥物治療感染性疾病的模式,是由一種令人難以啟齒的隱疾開啟的,這樣的治療模式在后來現代醫學逐漸成熟之后究竟拯救過多少條性命,早已經難以估算了。
但誰能想到這種挽救無數性命的治療模式,是由人們對一種性病的關注引發的呢?
梅毒是怎么來的?
性在滋生愛意和繁衍生命的同時,卻也傳播最令人厭惡的疾病,在這一大類疾病中,歷史上影響最大的——當屬梅毒。
人類對梅毒的關注,是從 15 世紀 90 年代開始的,但梅毒的準確的起源時間和具體的地理位置,仍然不清楚,美洲起源說和舊大陸起源說均有支持者,對于這一爭論,歷史學家似乎也樂此不疲,并沒有打算一錘定音由這一場爭論得出一個令各方信服的結論。
在無藥可用的年代,梅毒是兇險的,出于對這一疾病的恐懼,不同國家的人開始煞有介事地以此為由頭互相攻擊,將疾病暴發歸咎于特定的人群。
比如在 16 世紀,英國人堅信梅毒來自法國,因此稱其為法國花柳(French pox)。而法國人則堅信該病來自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因此稱其為那不勒斯病(Neapolitan disese)。在俄國,梅毒被稱為波蘭病(Polish disease)。在波蘭,這種病被稱為土耳其病(Turkish disease),土耳其則干脆把梅毒叫作基督徒病(Christian disease)。當這個病傳到中國時,中國人一度將這種病叫作廣瘡。
早期梅毒治療方式讓人糾結
著名醫學教育家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曾說:梅毒是高明的模仿者……誰通曉了梅毒,誰就通曉了醫學。這個說法是強調了梅毒的臨床多樣性復雜性,它在發病的不同階段能夠影響全身各個系統:一期梅毒會讓病人的外陰部出現硬下疳,二期梅毒會讓病人出現皮疹、發熱和廣泛的淋巴結腫大,三期梅毒的特征表現是皮膚、黏膜、骨骼和內臟器官的進行性破壞,最嚴重者會累及心血管(比傳說動脈瘤形成)和中樞系統(比如麻痹性癡呆)。
在由巴斯德和科赫開創的微生物學時代,一個又一個的致病微生物被鑒定出來,1905 年,德國動物學家弗里茲·邵定(Fritz Schaudinn,1871-1906)鎖定了梅毒的病因——一種線狀螺旋形細菌,醫學界后來將其命名為蒼白密螺旋體,次年,檢測梅毒的方法出現。
梅毒螺旋體 圖源:wikipedia
在當時,梅毒的治療手段卻非常有限,16 世紀時,巴拉賽爾蘇斯(1493-1541年)開始用汞治療梅毒,這種方法雖然能減輕部分梅毒造成的癥狀,可帶來的副作用卻也不比原發病對人體的傷害少多少,比如牙齒脫落、嚴重消化不良,甚至是死亡,屬于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療法。
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很多治療方式都是這樣,要么全然無效,要么利害相當,病人的選擇似乎只是在死于疾病和死于某位醫生之間來進行。那個時代的人,一旦遭遇疾病,治或不治,可真是夠讓人糾結的。
埃爾利希發現治療梅毒新藥物
對于疾病的治療,德國醫生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提出了一個非常誘人的思路,能不能設計出一種藥物,讓它只攻擊產生疾病的病原體,而對人體卻是安全的?
埃爾利希雜亂的工作室 。圖源: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
這一設想的理論依據是,化學物質在有機體內有特定的作用點,如果能找到與身體細胞沒有什么親和力卻與病原體有親和力的化學物質,那就能實現既可以殺死細菌又不損害人身體的目標。
為什么埃爾利希的腦子里會產生這樣一個思路呢?
原來他在研究組織染色的過程中發現,某種染料能夠將某組織染色與該染料與特定組織的化學親和力有關,也就是說,染料的生物效應依賴于該物質與組織中不同結構的親和力。埃爾利希據此推斷,那么,是不是就存在某種藥物,可以產生確定的生物學效應,卻不產生不希望出現的不良反應?畢竟,在實驗室中,理論上可以產生的化合物的數量似乎是無窮的。
從 1909 年開始,埃爾利希與助手秦佐八郎測試了許多化合物,最終發現編號為 606 的二羥基-二氨基-偶砷苯可以用來治療兔子的梅毒。但埃爾利希很清楚,很多看似有希望的藥物后來都因為效果不理想或副作用太嚴重而被放棄了,606 能成為治療梅毒的有效藥物嗎?
隨著后續試驗的不斷進行,606 越來越顯示出了治療梅毒的有效前景,為了推進臨床試驗的進行,研究所共生產了 65000 劑的藥物,免費提供給可信賴的醫生給梅毒病人使用。
到 1910 年時,參與試驗的醫生報告了大量治療成功的病例,埃爾利希發現 606 對新發梅毒效果較好,但對于晚期病例(比如已出現癱瘓者)效果就不那么理想了。此后,埃爾利希將 606 命名為灑爾佛散(salvarsan,意為治病的砷),希望能就此終結梅毒對人類的威脅。
新藥推行因副作用受到阻力
梅毒在歐洲流行了幾百年讓醫界束手無策,這從天而降的灑爾佛散沒有理由不受到熱烈的歡迎。但這一新藥在臨床推廣的過程中,也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很多人批評說灑爾佛散有嚴重的副作用,有些言辭極端的,實際上已經到了誹謗的程度,還有不少人認定灑爾佛散能給埃爾利希及制藥公司帶來巨額的收入。以至于埃爾利希不得不撰文回應公眾的質疑,要解釋研究測試新藥的過程中需要花費多么大的成本,他還得走上法庭通過訴訟手段以遏制嚴重的誹謗。
圖庫版權圖片,轉載使用可能引發版權糾紛
最離譜的反對應用灑爾佛散的聲音來自宗教界,一些宗教人士似乎是相信灑爾佛散能夠治療梅毒,但他們認定性病是上帝對凡人的懲罰,因此反對使用灑爾佛散。(類似的情形后來在艾滋病研究的過程中也出現過)
面對這些反對者的聲音,埃爾利希是清醒的,他沒有因為護短就故意無視或隱瞞灑爾佛散的副作用,到 1914 年,在全世界已經進行了幾十萬次灑爾佛散的治療,此間報道了 300 例嚴重的副作用,死亡率約有 1/1000。
要是現代藥物治療梅毒卻有 1/1000 的死亡率那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在當時選擇灑爾佛散治療梅毒那總比放棄不治或者選擇汞治療強太多太多了。
為了降低灑爾佛散的副作用,埃爾利希后來又與同事生產出了一種毒性較低的衍生物,1912 年這種衍生物被批準應用于臨床,名為新灑爾佛散。
埃爾利希一生獲得過無數榮譽,比如 1908 年因發現免疫血清的作用及創立“側鏈”學說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埃爾利希一生最重要的貢獻其實是在他獲諾獎之后才取得的。
1915 年 8 月 20 日,埃爾利希在先后經歷了兩次腦卒中后,再也沒有醒來。在他的葬禮上,他的好友埃米爾·馮·貝林在悼詞中說:死者已成為世界的導師,他是全世界醫學科學的老師。
科學家約翰·西蒙斯(John Simmons)將埃爾利希視為可與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科赫(Robert Koch)比肩的偉大人物,他認為:巴斯德和科赫開創了微生物學說,而保羅·埃爾利希 (Paul Ehrlich) 歸納出疾病的本質是化學。
如果說貝林的悼詞在當時的人聽來可能稍嫌肉麻的話,那么一百余年過去,我們站在今天的高度回望埃爾利希這位先驅所做的貢獻,就不得不認同貝林對他的評價了。
在今天,醫界在分子層面尋找解決問題的思路,完全就是由埃爾利希開創的,他對藥物可以殺死致病微生物卻對人體無害的設想,隨著百浪多息和青霉素等一系列藥物的先后出現,也徹底成為了現實。
推薦圖文
推薦資訊
點擊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