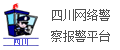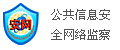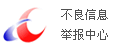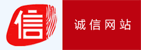鄉村運營 用上了CEO
核心提示:千村千面,可持續運營不能千村一面。每一個鄉村運營,都是量身定制。黃薈說。黃薈做過媒體,也曾是房地產企業高管,因創業夢與現
千村千面,可持續運營




“不能千村一面。每一個鄉村運營,都是量身定制。”黃薈說。
黃薈做過媒體,也曾是房地產企業高管,因創業夢與現實的差距,毅然辭職,從北京來到浙江。也因為喜愛鄉村,她選擇深耕鄉村運營。如今,她已是浙江資深的鄉村運營師和實踐者。

她介紹說,浙江的鄉村運營大致有三種模式。第一種偏傳統,由政府主導,出臺一些政策支持,主要以招商引資的方式打造一些項目。各個主體之間各自運營,只對自己的項目負責,不對村莊負責。
第二種,市場運營主體模式。村莊把所有資源通盤打包,委托專業運營公司整體運營。
第三種,鄉村職業經理人模式,即鄉村CEO。基本是區縣級政府主導,面向社會公開招募,進入由村集體主導成立的村企公司擔任CEO。CEO的工資部分由區財政撥款,部分由鄉鎮負責,還有一部分根據績效由村級公司再加一些獎勵,且上不封頂。
同時,運營方或CEO往往會在本地成立一個專業團隊長期駐扎在鄉村,優先招募本地年輕人。
一個村是否適合運營,不同的資源稟賦需要有不同的思路。
比如,她曾經服務過的三林村,地理位置較好,到杭州、蘇州等周邊城市距離近,符合1.5小時經濟圈要求,這是鄉村文旅的必要因素。村里的生態環境十分別致,有一片漂亮的湖,萬只白鷺在此聚集,形成“鳥類天堂”美景。后來,在團隊的運作下,去三林村觀鳥逐漸成為遠近皆知的玩法。
又比如,黃薈曾在梅林村策劃的鄉村脫口秀活動一經推出,深受行業人士和本地青年歡迎。正是因為她發現梅林村已有較多年輕人在村里創業、辦公,打造咖啡、文創等小業態,形成了一個青年社區,“脫口秀”是一個很好的文化切入點,借此能調動村中年輕人創造文化新生態的積極性。
又比如富春江沿岸的黃公望村,具有人文歷史底蘊,是一座實至名歸的文化村。黃薈在該村策劃運營的“公望書屋”項目,以書屋空間為主要抓手,把村里所有的文化資源植入進來,舉辦了讀書會、茶文化研習、親子活動等。“公望書屋”的活動直播在互聯網上有40萬流量。經常有名人名家去“公望書屋”舉辦沙龍,書屋每周往來人流比整村居民還多。由此,黃公望村吸引了一批文化人進村,開民宿,做文化空間等。這是把一個文化特色做深做透后,帶動整村資源的案例。
黃薈心中的理想圖景是,每一個村落,周周都有特色文化活動,一直可持續下去。顯然,它們需要專業運營團隊,需要人才長期駐扎在村里,才能做得成、做得大、做得久。

當整村資源一起盤活時
浙江南潯區舊館街道港胡村,有萬畝糧田與綠葉隨風逐細浪之景觀。
2019年,港胡村率先試點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與生態修復工程,3個月內完成簽約農戶309戶,簽約率達95%以上,為未來鄉村建設奠定了基礎。
黃薈與港胡村的合作模式是第二種,市場運營主體進入鄉村,負責對整村資源進行盤活。她帶記者參觀正在招商階段的古村落,以及即將建成的“港胡青年國際鄉創學院”。學院的前身是村里的菜市場。由于古村居民遷至新居,村落大量的閑置空間可以重新規劃利用。黃薈從頂層設計角度,通盤考慮村莊的資源優勢,為村莊提報了策劃運營方案,村集體表決通過后開始執行。方案具體到空間設計、施工、采購以及青年入鄉計劃、鄉創人才引進、產業開發、市場推廣等各個環節,后續也由她帶領團隊負責運營。黃薈還為古村落的一天如何玩,設計了一套“古村十二時辰”方案,供后續宣傳使用。
也就是說,因為把整村運營委托給了黃薈,她在項目早期就參與了大量意見,包括設計和執行,使得后續運營的文化內容與設計高度匹配。“運營前置、文化引領、產業導入、傳播助力”,這四步被她稱為鄉村運營的“方法論”。
港胡村黨總支書記錢建強告訴記者,村里整體資源盤活后,做了四類模式探索。探索土地流轉雙贏模式,他們連片整合打造萬畝糧田示范區,引進星光高品質數字糧油示范基地項目,通過公司+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實現農戶畝均增收超300元;探索綠色產業模式,他們利用土整后的零星土地,開發林下空間、眾創攝影基地及野塘嬉戲等綠色觀光產業,解決了120余名村民就業;探索資產盤活模式,他們利用港廊古村落中騰空的老宅,引入民宿、咖吧等業態,將古村落文旅資源與農業資源有機結合,打造田園農旅研學綜合體,實現增值增收,村集體現有經營性收入超250萬元;探索人居環境模式,他們利用善治積分和獲選者每月獎勵10斤大米等,由老百姓自己打理人居環境,保持小區干凈整潔。
浙江余杭區永安村,則采用了第三種模式,即村集體企業招聘CEO。
劉松大學的專業是農業,此后在一家大型民營企業上班。機緣巧合下,他成功應聘,成為永安村村集體企業杭州稻香小鎮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的CEO。
劉松初來乍到時,第一次對永安村資源進行排摸,發現運營難度很高。原來,村里農田97%都是永久基本農田,法律規定絕不能動。相當于這個村就沒有什么“閑置資源”可挖。村民世代種糧,集體收入較低,是附近出了名的“窮村”。
“我們意識到,永安村只能圍繞水稻來做文章。”劉松說。他和村黨總支書記張水寶商量后,確立了兩個重要方向:做水稻產業,一是品牌化,有品牌才有影響力,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二是數字化,必須與時俱進,與數字時代接軌。目標是把永安村打造為一個水稻全產業鏈示范村。
擼起袖子加油干。村集體企業成立后,張水寶擔任董事長,劉松擔任職業經理人。他們給永安村的糧食品種、標準、種植范圍等制定了一套指標,把種子買好,交到農民手上。哪幾戶需要種哪些品種、種多少、怎么種,全部按標準化、機械化生產的要求來。隨后根據設定好的計劃,從農戶手里收購,找到第三方企業進行加工。永安村的水稻品牌,除了高端大米以外,還開發了米酒、米類飲料、米制零食等,全部進行市場化銷售。如今,開發的大米和大米衍生品25種,認養稻田的企業數量68家,研學類課程48個,整合周邊農產品35款,帶動14名本地村民回鄉創業。
在數字化上,一方面劉松自己帶頭在線上平臺直播銷售,另一方面對生產進行全程數字化管理。在永安村的文化禮堂里,有一面科技大屏,能遠程看到水稻情況、農田氣象、土壤數據等。原來,稻田被裝上了監控,數據得以實時傳送到消費端——購買大米的消費者掃描包裝上的“農安碼”,就能看到稻田的真實面貌。
有了鄉村運營,永安村集體經營性收入由2019年的73萬元提升至2023年的550萬元,村民人均收入由2019年的4.2萬元提升至2023年的6.3萬元。
“我們要做的是農民做不了的事情。”劉松解釋說,農民依然負責生產,他們負責制定標準、設計、市場推廣和營銷。劉松的工資由底薪+績效+分成組成,與績效掛鉤。他還為公司專門招聘了約30個人的市場營銷團隊。團隊成員基本為“90后”,普遍居住在這片區域,只有兩人沒有在此安家。而這些年輕人中,2/3原本在大型企業和上市企業工作,不乏具有研究生學歷者。
“能夠回家鄉工作,為家鄉做推廣,每天看到窗外的美景,不在大廠卷,我很開心。”一名“90后”員工這樣說,并且自認為“吸引我們的最大魅力在于價值觀”,這份工作讓她有一種榮譽感和歸屬感。
劉松自豪地說,5年里,這支年輕團隊幾乎沒有人離開,大家喜歡在村里上班。
劉松還為下轄的每個村落招聘了“鄉村造夢師”。他們普遍比較年輕,長期駐扎在村里。
如今,這片永久性農田保護區有個響亮的名字“禹上稻鄉”。劉松和永安村村集體企業參與了全國第一個鄉村CEO標準制定。永安村的土地上,新建起鄉創培訓中心,周邊越來越多的村落開始抱團加入。

鄉村振興不靠“公式”
江南氣候溫潤,豐衣足食,水系發達。古有“蘇松熟,天下足”的諺語。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王海松說,上海的江南底蘊得益于都市發展。上海一直是五方雜處、不同文化雜糅生長的創新之地。滬派江南村落是現代化生活中人們仍然愿意親近自然的態度的投射,是江南和世界接軌的窗口。滬派江南需要留住的不只是水、田、林,還有本土植物、本土生活和生產方式、獨特的人居環境等。所以他并不提倡單純用現代造景手法,營造那種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快速復制的鄉村風貌。
因為這些特征,上海鄉村運營需要一大批人去摸索、去實踐,很難完全復制哪種模式。更重要的是陪伴式成長,駐扎在村里謀發展,而不是待在城市里指指點點。
“由專業人士來運營,對全村資源整體評估,統籌制定運營方案,這套模式上海可以部分借鑒。”上海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鄉村規劃處處長顧守柏說。
在他看來,整村資源通盤考慮確實有一定優勢。上海鄉村作為大都市的鄉村,其資產價值更加顯化,也更多元化,尤其是農民的住房、村級的經營性空間等,是搶手的香餑餑。
此前,涉及這些資源,外來主體必須與鎮村集體或業主一對一打交道。目前,有關部門正在探索一種更新的模式,比如是否可以統一搭建平臺,統籌發布相關的農戶房屋、其他鄉村經營性空間資源資產租賃等信息和內容,公開透明,合理配置公共服務功能,一體化管理。如此,村級資產能更加符合市場準入機制要求。

顧守柏也提到,討論滬派江南的“三師聯創”機制時,專家們就意識到,不僅需要規劃師、景觀師、設計師聯動參與,也需要產業運營團隊提前介入,策劃先行。但是運營團隊的模式是什么?很難統一推介。大都市鄉村的整村運營涉及更多門類,產業項目的資源配置也更加復合,每個村的資源稟賦又不盡相同。“量身定做”“因地制宜”才是不變的宗旨,必須多元參與,多師團隊密切配合。
鄉村運營有時候關鍵在于能人,難以提煉“統一公式”。甚至村領導的專業擅長等因素,都會影響運營模式的走向。有一種聲音認為,上海的基層干部聰明能干,很有想法,反倒不放心將村莊完全托給一個外來團隊來打造。但基層政府的主要職能還是政務,運營難以投入全部精力。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是一條黃金法則。
有意思的是,劉松一直反復強調,不是CEO來運營才有鄉村振興,而是先有鄉村振興,才有他發揮的舞臺。
永安村過去只有一條3米寬的泥路。張水寶擔任村黨總支書記以來,先是修路、改造灌溉設備等,把七零八碎的土地連成片,為規模化種植奠定了基礎。再是將土地集中流轉到村集體,發包給專業大戶,機械化生產。有了這些基礎后,張水寶有感于自己的管理水平可以,但缺乏市場思維,苦尋專業人才而不得。直到2020年,《關于加強余杭區農村職業經理人培育工作的實施辦法》發布,政策為鄉村CEO制度指明了方向,這才有了后面劉松的上任。鄉村運營中,政府究竟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這便是一個有價值的案例。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及一個觀點:對鄉村振興不能期待過高。比如說,一定要做成人流爆款,呈現一派熱鬧景象,甚至成為網紅,才叫振興。那樣的超常規走紅,反而大多是不可持續的。
無論是上海還是浙江的受訪者,在大家心中,只要農民居住質量、生活質量、公共服務配套質量有保障和提高,鄉村生態基底不被破壞,農業穩定發展,再進一步有一些空間資源的盤活,已經算是走在鄉村振興的路上了。畢竟,行穩致遠,和合美好,是鄉村振興的終極愿景。
推薦圖文
推薦資訊
點擊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