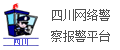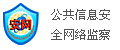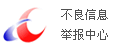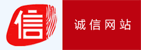陳毅之子回母校組織文革道歉會 向老師鞠躬
白色長桌的一邊坐著8名曾經的中學教師,頭發白了;另一邊坐著15名曾經的學生,頭發大多也已經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學對面一間茶社的會議室里,空間局促,暗淡的燈光照在老人們的臉上。
“在座的,張顯傳老師80歲了,大部分老師也都70多歲了。連我們這些學生年齡最小的也有60歲了,已經過了耳順,而你們都是古來稀了。像曹操講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話不說,就太晚了。”穿著藍格布襯衫的陳小魯第一個發言。他的頭發已經全白,皺紋也深陷在臉上。
此前他曾經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實際上已經有點遲了,為什么這么晚才公開道歉,因為你過去不愿意面對這個歷史。”那時候他的語氣還顯得很平靜。
但在這一天的道歉會現場,他的情緒則有點激動。陳小魯放下手中備好的講稿,大聲地致開場詞:“‘文革’之后,老師對我們的冒犯寬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當年傷害過你們的校友,向你們真摯地道歉!”
這已經不是陳小魯第一次向老師表達歉意。過去在校慶活動時,他曾經專門走到幾位當年遭受批斗的校領導面前親口致歉:“老師對不起了,當年讓你受苦了。”但他漸漸覺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還欠老師一個“公開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學計三猛專門給擔任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會長的陳小魯打來電話。他說自己前幾天回學校看望老師,當年的生物老師趙榮尊告訴他,“當年教過你們的老師,每年都有去世的,一個個地都凋零了。”
老師的話讓計三猛和陳小魯感到,“再不道歉就來不及了”,組織一場聚會的想法也由此產生。后來陳小魯曾把他們商議此事的郵件轉發給記者,那時他就有送一封信給老師的想法,有感謝,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長,情真意切就行”。
陳小魯沒有想到,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會在不久后引起關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為陳小魯的“道歉信”出現在“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用作內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這樣寫道:“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正在安排一次與老校領導和老師的聚會,我希望能代表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的老三屆校友向他們鄭重道歉,不知道校友們是否授權我做這樣一個道歉?”
后來,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體發現,并被擬上了“陳毅之子陳小魯就文革中批斗學校領導發道歉信”的題目,隨后在網絡中廣為流傳。
“很多記者給我打電話,家里人也說,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陳小魯事后回憶。
“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這封所謂的“公開道歉信”其實只是陳小魯回給同學會秘書長黃堅的一封私人郵件。
“我收到了黃堅發給我的一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領導被當做黑幫批斗和勞改時的情景。”陳小魯記得,黃堅在郵件的最后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歷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們今天——一個歷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從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師們說一聲:對不起您了,我們真誠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那一天,陳小魯和上百萬人齊聲高喊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走向廣場。
陳小魯看著已經泛黃的照片,記憶越來越接近1966年。
一張照片里,幾百名學生聚集在教學樓中間的大院里,兩名戴眼鏡的女教師正低著頭站在水泥臺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師舉著一塊小黑板,上面用粉筆寫著“黑幫分子”四個字。身后的平房上,則掛著寫有“永遠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字樣的條幅。
陳小魯依稀認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師正是黨支部書記華錦。
那一年陳小魯剛滿20歲,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點中學,學生中大約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稱作“政治起家”的學校。
回憶當年,陳小魯笑稱自己“左得很”,整天學的都是“階級斗爭”、“反修防修”這些東西。“文革”爆發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傳說,毛主席講,學校已經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了。
“當時就想,誰統治啊?肯定不是學生啊,那只能是校領導吧!”那一年,陳小魯在墻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寫的是“讓階級斗爭的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發,學校停課。6月9日,一張大字報貼在八中里,揭發說學校的一個工友因生活艱難而賣血。“這在當時是很煽情的,我們覺得校領導太沒有階級感情了。”陳小魯記得,當時全校群情激憤,學生們把校領導揪到水泥臺上批斗,底下站滿了人,有的初中生還戴著紅領巾。
校領導靠邊站后,陳小魯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學生里的領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師大會上代表學生講話:“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后來,各個學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則成立“校文革”并選舉了革委會主任。在八中,陳小魯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滿票通過。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
“文革”爆發時,黃堅也在念高中。當時流行一句話是“好人斗壞人,活該;壞人斗壞人,狗咬狗;壞人斗好人,經受鍛煉;好人斗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 黃堅親眼看到校領導被學生掄著皮帶追打,有人還振振有詞: “這是考驗我們革命不革命的時候”。這種恐懼延續至今,在中國青年報記者的一次電話采訪中,他曾在回憶往事時一度哽咽得說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為迎接90周年校慶有了籌建校史館的打算,黃堅一下子收到了許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來發給陳小魯那組。但當時黃堅清楚,“這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選上”,便拿相機把它翻拍下來。
陳小魯很快回復黃堅,郵件里寫道:“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凈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第二天,8月19日,黃堅將這封回信放到了同學會的博客上。
“我確實沒想到,他看到這個東西后會有這么明確的表態。”黃堅說,此前也曾接觸過私下里向老師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師道歉”。但陳小魯的反應仍然讓他感到“很不簡單”,“因為陳小魯本人并沒有打過人,他也公開反對打人”。
他們的老師趙榮尊曾經提起,當年,幾個初中學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給她戴高帽、剃陰陽頭。湊巧路過的陳小魯攔下了這些少年,“你們可以批,但不許揪斗,不許剃頭”。后來,趙榮尊挨了一個多小時的批,陳小魯也陪在她身邊站了一個多小時。
“經過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嚴,有他的權利,是受憲法保護的,但當時我不知道這些。”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陳小魯坦率地說道,“我那時候只是有個樸素的認識,黨的傳統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里有一條,不能虐待俘虜!”
但北京八中的局勢還是一天天變壞下去。那時候,社會學家鄭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選革委會主任的時候,他還投了陳小魯一票。 “我敢說,打人的事情,當時在校的所有學生,沒有人不曾目睹過。”鄭也夫親眼看到,一個常年患病、平時不來學校的“右派”老師,因領工資來校時,被在全校打人“名氣最大”的一個高二年級的紅衛兵截住,兩人面對面時,“就像羊面對狼一樣,老師眼里的那種恐懼,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最后這位老師遭到一頓暴打。
死亡很快發生了。一天,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上吊自殺。此前,一名學生曾經在校園里遇到過她。“我受不了了。”華錦對他說。陳小魯至今都記得,自己趕到學校南側的那個教室里時,華錦全身浮腫,一動不動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斗、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斗過校領導,后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文革’,那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
47年后,陳小魯在回復給黃堅的信中這樣寫道。
“八中有1000多個學生,是每個人都造反了嗎?是每個人都去積極批斗老師了嗎?沒有啊!”
“當時老三屆同學會內部反應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覺得小魯有點矯情,還有人提出,要站出來道歉的應該是當年打過人的學生,而不應該是他。”計三猛回憶起此事被公開后的情形。
8月24日,學者張鳴發表了一篇題為《對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懺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寫道:“不止‘紅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或深或淺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參與過傷害別人……但是,不知怎么一來,所有人突然之間都變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個民族,幾億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這樣一來,一場持續十年、卷入幾億人的災難,除了幾個死掉和在監獄里的人之外,在現實生活中,就沒有了加害者。”
采訪中,陳小魯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我是沒有打人,但我還是造反了,這一條我就錯了。你可以推脫,說那是大環境的錯,不是我的錯。這也對。但是這件事情就發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個學生,是每個人都造反了嗎?是每個人都去積極批斗老師了嗎?沒有啊。我也可以選擇不挑頭,但我還是參與了,而且是帶頭的呀!”
“他就講,正式道歉這個事情很重要,要盡快做。對那些身體不好走不動的老師,他想登門拜訪,一個個去看。”黃堅記得,在這件事成為輿論焦點后的第三天,陳小魯就和他們相約前往海淀區的陽臺山老年公寓,那是當年的教育處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魯要來看我吧。”在電話里,李阿玲似乎已經知道他們的來意。那一天,86歲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門口等待自己的學生們。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們。”滿頭銀發的李阿玲給陳小魯拉來一把椅子,讓他坐在自己的對面。
“老師對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寬容。”黃堅說,相比于“文革”時受過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憶那些人性中的溫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門口被一幫學生們圍住,結果一個老師遠遠趕過來喊,“你這個黑幫分子,還不趕快給我滾蛋!”接著,這個老師還騎著自行車在后面追她,“后來我才知道,其實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趕快到前面去攔7路汽車,讓我趕緊跑”。
知道學生們要來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長溫寒江也很高興。他89歲了,但交談起來仍然興致勃勃。只有在偶爾提起那段舊時光時,他臉上的神采才整個兒黯淡下來,“音樂堂那次批判會之后,我被打了3個小時,很痛苦……”
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會在中山公園的音樂堂里舉行,參與者是來自“四、六、八中”的學生,站在臺上接受批判的“黑線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書記張文松、局長李晨以及幾個西城區重點中學的校領導。
作為這場批判會的組織者,陳小魯起初的想法很單純,“那時候要‘找題目’,總要找個事情搞一搞運動”,他原以為,“開批判會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號”。
意外很快發生了。黃堅當時坐在音樂廳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學生就沖上了主席臺,掄起皮帶就抽,看得我們膽戰心驚!”
“沒辦法了,擋不住的”,主席臺上的陳小魯舉起紅衛兵的旗子,朝著那些沖上臺的學生喊口號,“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
“連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嚴的口號。”提起那段往事,陳小魯唏噓不已。也正是在經歷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開始由“造反”轉向“保守”。
“那次批判會是我組織的,影響很壞,因此我想向您當面道歉。”陳小魯接過老校長的話茬,說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對不起”。
“這不能怪你們,當時你們還是文明的。”溫寒江擺了擺手,平靜地說,“‘文革’中的錯誤不能簡單歸咎于哪個人,更不能由你們這些學生負責。”
黃堅舉起相機,拍下了師生和解的這一幕。照片里的溫寒江的確已經老了,他的腰背開始彎曲,連眉毛都掉得很厲害。坐在他身邊的5個學生也不再年輕,他們中的三個人有了嚴重的謝頂,另外兩個人則已滿頭白發。像很多這個年紀的老年人一樣,他們開始耳背,有時會聽不清對方的講話。
幾天后,黃堅把當時的情形整理成文發在了老三屆同學會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剛被診斷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幾十粒藥,但他還是把大部分時間放在了張羅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們就都太老了。”他說。
“我們不說,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老師,對不起后人和歷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會之前,陳小魯接到一個《紐約時報》女記者打來的電話。
“陳先生,我曾經采訪過你的父親,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電話那頭的聲音已經不再年輕。
幾天后,這名70多歲的老記者如愿見到了陳毅的兒子、也已經年近70的陳小魯。
“那時我很幼稚。”她告訴陳小魯,自己是澳大利亞人,當時是一名左派大學生,1967年她慕名來到中國,并在陳毅兼任外交部長期間,得到過他的親自接見。在中國的時候,她也穿軍大衣、戴紅袖章,打著紅旗到處參觀。
這種歷史戲劇性同樣存在于陳小魯身上。一個曾與他在“文革”期間有過通信往來的學者認為,“陳小魯的這種政治態度和立場代表了一批人,特別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響應毛澤東號召起來‘造反’,又最早對發動‘文革’表示懷疑直至否定的人們。”
1971年“9.13林彪墜機”事件是陳小魯思想轉變過程中的又一個節點。“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為什么還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飽了撐的?”陳小魯有了一個解不開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興起,作為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團政治部主任,陳小魯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鄧”。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給岳父粟裕寫了一封信申請調動。“道不同不相與謀”,他在信里寫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錯,但那時候不是了,搞這一套我自己心里頭接受不了。”陳小魯說,從那時開始他已經“不想再說違心的話了”。某種意義上,這種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軌跡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與體制告別,下海經商,自稱“無上級個人”。及至今天,這種民間身份則間接幫助他可以選擇公開向歷史低頭致歉。
“已經47年了,將近半個世紀,經歷了風風雨雨,開始一步步反思,當時覺得‘文革’是政治錯誤,后來發現它的根本問題在于違憲。”10月7日,坐在茶社會議室的紅色沙發上聊起這些時,陳小魯顯得憂心忡忡。他開始主動談論當下,反復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車打同胞的年輕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經消除了?類似的東西會不會再發生?很難說。”
“就像帕金森病一樣。”陳小魯拿起擺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個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說是失誤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問題,不正視,怎么解決?”
陳小魯看重反思,卻反感輿論“將道歉者崇高化”,“每個人都是在書寫自己的歷史,這只是我的個人選擇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認為是這樣。真正的反思不見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經歷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
在眾多接受采訪的當事人里,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秘書長郝新平對那段狂熱的歲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為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門城樓上獲得了毛澤東的接見。而就在那次接見的13天之前,這個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學生打死,成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個遇難的校領導。那一天,郝新平親眼看見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車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發捐款為卞仲耘立了一尊銅像。“也有同學私下里向還在世的校領導道過歉,但打人者都背著很重的包袱,到現在也沒有人敢于站出來為此公開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魯的事后很受觸動,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給社會歷史一個交代。”郝新平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自己曾經發短信詢問陳小魯關于公開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陳的回復:“遺忘是人類的天性,九零后有幾人了解這段歷史?我們不說,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老師,對不起后人和歷史。”
“我挺希望他們能了解那段歷史,哪怕知道我們八中曾有過這么一段黑暗的時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歲年紀的人一樣,當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談論著身體近況、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霧霾天氣。只是在一些特別的時候,他們的對話里才會透露出這場聚會的不同之處。比如,當他們分成兩排落座時,忽然有一個老人問起另一個老人:“咦,我是不是教過你?”
47年后,老師不再像是老師,學生也不再像是學生。他們的年齡之和已經超過1500歲,而相互之間的年齡界限卻不再那么分明,白發、老年斑以及日漸松動的牙齒同時在他們的身上顯示著歲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這場聚會上,他們又部分恢復了往日的神采。年輕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們出現在一張張的照片里,在會議室內的投影屏幕上反復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著,有的老人被旁邊的擋住了視線,就用手拄住桌,探著頭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來。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憶的好時光。許多人找到了他們第一天走進校園時的樣子,另一些人則回想起這個曾經的男中頭一回迎來女生時的熱鬧。
循環播放的照片里并沒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這是播放者黃堅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殘酷的回憶還是會在不經意間就冒出頭來。老團委書記張慶豐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時被學生叫到音樂教室接受審查,他被要求“從窗戶里爬進去爬出來再爬進去”,回家后這個大男人哭了兩個小時。當年的物理老師張連元剛一張嘴,就忍不住哽咽起來。“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問題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學的人民教師,于1968年墜樓身亡并被學校視為“畏罪自殺”。
在將近3個小時的道歉會上,僅有這兩次,老師們流露出了內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時間里,他們并不愿自己的學生執著于道歉這件事。
“沒有必要站出來道歉,你們也是受害者,當年是階級斗爭為綱,誰能不擁護?”年紀最大的老師張顯傳第一個發言。坐在他旁邊的老黨總支書記盧進則說,“老師對待學生,就像父母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學生犯再大的錯誤,我們也能理解。”
“沒有必要追究你們的責任。”張連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淚。他抬起頭,像是叮囑般地說道:“但是要總結這一段歷史,把法治建設提到重點,今后不再出現類似的問題。各位,我們希望你們能在這方面進一步作出應有的成績。”
面對老師的諒解,陳小魯和其他幾個校友沒有再多說什么。在聚會結束的時候,計三猛忽然大聲說了一句:“感謝老師的教育!感謝老師的寬容!”
所有到場的老學生,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向坐在對面的老師們深鞠一躬。
道歉會結束后,陳小魯領著中國青年報記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東西已經改變了。曾經的胡同平房已經變成金融街的高樓大廈,水泥地操場也被一座奧運會級別的現代化體育館所取代。但陳小魯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回當年的記憶。
1966年8月的一天,學生領袖陳小魯和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一起,走出校門,穿過胡同,前往中山公園音樂堂。為了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陳小魯組織了這場“四、六、八中”全部參加的批判會。他并沒有想到,幾個小時后,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會被一群突然沖上臺來的中學生打得頭破血流。
講起這段往事時,陳小魯朝校園里看了一眼。國慶長假還沒有結束,除了幾個保安之外,學校里空空蕩蕩的。
“現在的孩子們可能對‘文革’沒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們能了解那段歷史,哪怕知道我們八中曾有過這么一段黑暗的時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這段歷史,不要斗爭老師,不要斗爭任何人。”陳小魯嘆了口氣,從刻著“北京八中”四個大字的校門前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