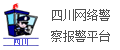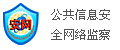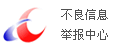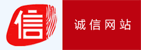優步,把美國理想主義還給我
在一款打車軟件里,我們看到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差距,或者全球一體化的魔幻現實主義在上演。至少當我聽到一個優步司機,用帶口音的普通話大聲問我:“什么是星巴克,是不是那個綠色女人頭?”的時候,我聽見自己幻像破滅的聲音。

一,Uber
第一次坐Uber是到舊金山看一位朋友,拜訪結束,朋友給我打了輛Uber去機場。
開車的是個ABC美國華裔男生,車內舒適干凈,音響是頂配,車門的儲物盒里還裝滿了各種零食。我好奇的東看西看,司機說:“我太太坐車喜歡吃零食,你也不用客氣。”知道我在這座城市停留了不到24個小時,他特地給我介紹周圍的景觀,還有房價。他叫Jason,三十出頭,全職工作是Verizon(美國的一家電信公司)的店面經理,手下有4,5名員工。一個星期工作6天,第7天倒休還來開Uber。問他,“不辛苦嗎?”他說,和太太結婚買了房子,但是這幾年舊金山的房價被網絡新貴炒的很高,雖然他和太太都有不錯的工作,沒有孩子,但每個月還房貸有很大的壓力。他太太是一名中級會計,沒有拿到會計師證書,他們兩個的稅前收入應該在10萬-15萬之間,已經算是這個年紀收入不錯的美國白領。
每星期一天當Uber司機帶給他一個月1千美金左右的額外收入,對此他還算滿意。我問他,如果未來要孩子還會當Uber司機嗎?他在機場的送客坪回頭看了看身后的城市,說:“到時候,我們可能會搬到一個小鎮上。”

我沒有想明白整個事情的邏輯:網絡公司的新貴們(朋友公司的所在地就是Airbnb和Twitter總部所在的街區)炒高了整個城市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但同時又提供了Uber這樣的自由職業者的工作和收入,或許還有一種尊嚴。
這是一種補償還是一種因果?
《紐約時報》的一篇“未來你可以會像Uber司機一樣接單”的文章中說“你也許沒有在近期內成為Uber司機的想法,但是你所選擇的職業可能很快就會被Uber化。”像是對Jason的生活狀態的解答,文章說,美國工資停滯不前,Uber這種按需求而存在的經濟模式可能提供另外一種經濟來源。同時,技術會讓我們的工作生活更有彈性,讓我們根據自己的時間來安排一個或多個工作,而不是根據工作來安排自己的時間。
這些經濟學式的分析遠不如我看過的另外一篇雜志報道來得浪漫。報道中的美國Uber司機告訴乘客,他不是一名司機而是一名珠寶設計師,拉開車里的工具箱,是他的珠寶設計樣品,乘車的空暇還可以看他的制作精美的珠寶畫冊。這份自由司機的工作成了一輛行駛的展示臺。
這些美國媒體認為,Uber不僅僅是出行工具,它可以賣更多東西,給人們更多自由的選擇。

“未來可能會是這樣的——一小部分勞動力會以做很多不同的工作為生:你可以做Uber司機,替Instacart買東西,在Airbnb上租房子以及在Taskrabbit上攬外包”。
二,人民優步
一開始沒有在北京用優步, 因為每次都是出差,聽說Uber不提供收據,無法報銷。但是我勸一個人到中年迷上烤面包的哥哥,去當Uber司機吧,車后箱裝一箱剛烤出爐的法棍,多棒。
正式下載UberApps是在“神舟”黑它的時候,感覺自己充滿了正義感,而人民優步---多么充滿了人文主義、代表著美國的FreeSpirits。
幾天后,有一晚在大望路的新光天地。電話里接單的司機問:新光天地在哪兒?我說,大望橋,正北,標志是SPK。對方說,不知道,我按導航找你吧。手機顯示的是3分鐘路程,7,8分鐘后打電話給他,他說“在掉頭”。10分鐘后打電話,他還說“在掉頭。”然后問我,“你到底在大望路哪邊呀?”我又解釋了幾句,發現他還不知道,就打算取消了。對方說:“好”。
剛放下電話沒多久,手機短信顯示,我被扣了8.80元。
我等了他10多分鐘,他依然沒有到達指定地點,甚至在標示這么明顯的一個路口。我打電話過去理論,司機說:“我已經在掉頭了。”外地的口音極為強硬。我準備打電話投訴他,最后發現只能發郵件,這種投訴太不方便,于是作罷。
還有一回是去“繁星劇場”參加一個正式活動。我在打車的時終點輸入了繁星劇場,最后選擇了“宣武門內大街繁星劇場”。很快一輛寶馬5系列把我拉到了國家大劇院東邊,我雖然是北京人,但自從北京奧運后就失去了對北京方向感的自信。不過我還是覺得不對勁,我問:“師傅這是國家大劇院,我不是要去繁星劇場嗎?”開車的師傅非常肯定的說,“這就是,下車”。而且把手機上的優步導航拿給我看,導航上標注著我們所在地點就是繁星劇場—中文,明明白白,毫無歧義。我頭想了想,對一個軟件定位技術的信任完全壓倒了一個北京土著對家鄉的方位判斷。于是我下車,穿過一條很寬的人行道,繞到大水蛋前方,下樓梯……我想說的是,那可是38,9度的氣溫,加上我穿著一雙7寸的高跟。等到了國家大劇院的購票處,汗如雨下的問工作人員,繁星劇場在里面嗎?工作人員看著我像看著剛剛完成一場長跑的阿甘一樣。
后來發生類似的事,是司機找不到我的地點,聽到過他們抱怨這個導航定位有問題,我總想起那個把我拉到國家大劇院,把手機導航舉在我面前的司機。繁星劇院和國家大劇院至少差10分站的車程吧,怎么差出來的我到現在也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我遇到的優步司機10個里面有8個不是北京人(甚至不是北京郊區人),他們操著外地口音,一天工作10個小時。有的新車也是他們為了當優步司機,借錢買的。

最后一次是我在嘉里中心,司機很快來了,打電話問我:“嘉里中心的什么地方?”我說“嘉里中心的星巴克。”那邊傳來很大的聲音問我:“星巴克是什么?”我說,星巴克咖啡!司機重復著:“什么星巴克咖啡?我看見一個綠色的女人頭,是不是?你在附近嗎?”
我當時愣在哪里,手握電話,無以應對。我以為自己支持的是一種具有美國的自由主義精神--“FreeSpirits”, 但這樣東西,和大部分中國優步司機可能沒有一毛錢的關系。因為我明明在北京繁華的CBD,碰到過認不清大望路和新光天地的司機,還碰到過管“星巴克”叫綠色女人頭的司機……他們可能為一款打車軟件,和傳說的高收入,背井離鄉,成為優步北漂。人民的優步,戴上了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帽子,和美國城市尋找多元化工作的白領,自由自業者,獨立的靈魂,舉著火炬的女神只有每接一單的補貼關系。
這完全不是那些優步北漂司機的錯,是我們這些打車的人把理想主義強加到了一個供需非常赤裸裸,所有生計全部來自于開優步的人群身上。據說,很多Uber司機其實有兩套軟件,滴滴和Uber都同時接單。
像很多外企在中國受到本土化的沖擊和阻礙一樣,不過中國優步和美國的Uber相差太遠。這是不是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太大,城鄉勞動力的素質差距太大,我們解決的不是工資停滯的白領問題而是巨大的勞動市場和失業率問題?還是中國的商業運作到今天為止最好不要和精神強加聯系?
你為什么不告訴我,滴滴和優步其實沒用什么大的區別呢?
在一款打車軟件里,我們看到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差距,或者全球一體化的魔幻現實主義在上演。至少當我聽到一個優步司機,用帶口音的普通話大聲問我:“什么是星巴克,是不是那個綠色女人頭?”的時候,我聽見自己幻像破滅的聲音。
據說今天是優步進入中國一周年,我不是來來砸場子的,我是來砸理想主義者,和販賣理想主義者的。
醒醒,把美國理想主義還給我!